“中国通史”写作像中国历史学一样悠久,孔子整理《春秋》,孔门记录三传,墨子阅读“百国春秋”,均表明中国人的通史意识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等《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
进入近代,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鼓吹“史学”,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新型中国通史的开篇之作。他的思想得益于他的朋友严复,至于著述体例、表达方式,很明显受到梁启超、章太炎二人的影响。
进入,用新方法、新思写作中国通史蔚然成风,相当一部分大学者都有重写中国通史的冲动,即便以考史擅长,以断代擅胜的陈寅恪,对中国通史的编写也相当重视,对自夏曾佑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品,似乎都有涉猎,且有点评,[2]甚至有意动手写作一部中国通史以为典范。可惜由于各种原因,陈寅恪除了在课堂上讲述过中国通史的某些断代外,并没有更详细的中国通史作品。
陈寅恪没有致力于中国通史写作,除了个人兴趣、时间、身体诸多原因,还有一个背景必须注意,即学风的转移。据钱穆回忆:“从前我中学毕业,回学校请教一位老师吕思勉先生,一部二十四史如何读法?他说:这极省力。他便帮我计算,一天读多少卷,几年一部二十四史读完了。我这是学我中学先生的方法。现在诸位不这样,诸位看不起通史,要讲专史。不但只研究一部专史,而且是在一部专史中挑选一个小题目,来写篇几十万字的论文,才能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这样便做不成学问。我们今天走的西汉人的。诸位或说,我们今天是走的美国人的,美国人的其实便已走错了。”[3]假如我们注意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情形,但凡留学归来的,除胡适、张荫麟、蒋廷黻等极少数具有宽广视域愿意写作通史、通论,更多的学者无不像钱穆所讥讽的那样,选个小题目做个中等规模的论文。
其实从学术史角度说,钱穆的说法最具,中国历史学从来的数都是贯通,是由博而约。传统中国学者的正当学术径是博览群书,打下一个广博的基础,然后再凭借个人兴致或述史,或考史。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孔子时代写通史,需要阅读、鉴别的史料远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时简单得多。到了宋代,要想完成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司马光就必须成立一个班子,从长编开始做起,否则没有办法穷尽相关史料。须知,司马光的时代,造纸术、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使用,人类积淀的文献尽管很多,但毕竟仍可以大致穷尽。
宋代之后,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即便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也开始向各个专门学科用力。在六朝各种典制,尤其是唐学者杜佑《通典》基础上,宋元学者马端临发展出《文献通考》,南宋学者郑樵发展出《通志》。这三部作品后来统称为“三通”,进而演化成“九通”、“十通”。在某种意义上说,“十通”表明人类知识急剧增长,包罗万象的通史编写越来越难,对史学家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梁启超虽然都信誓旦旦要编写自己的中国通史,但他们事实上都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无法着手,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前人留下的史料太多了,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不要说近代以来突然增加的卜辞、敦煌文献、大内档案、满文老档,即便史书,即便卷帙有限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真正读完的又有几人?因而20世纪中国历史学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学术分化越来越严重,分科研究,专精的小题目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综合研究,整合研究越来越大,越来越闳大不经。一部新编断代史可以多达数千万字,一部专门通史可以数千万元立项,其实如果从学术史视阈去观察,将来的学术史家一定会追问,没有全面细致的史料阅读,没有贯通理解,这些大型项目的主持者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在细节上突破呢?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出版了大批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这些史书在那个特殊时代对于现代人理解古代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些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无不出于主题先行,或以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叙事的主题,因为据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或以作为中国历史叙事基调,因为经典作家认为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或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的作为近代史叙述主线,因为经典作家不仅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近代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而且是近代中国不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些先行的主题规范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通史、近代史的基本样式,然而由此却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难道历史真的不是客观存在吗,难道历史真的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一定有一个,历史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并不因为历史学家推崇农民战争,就成为农民战争史。历史某一个主题被刻意放大,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之前,并没有对历史文献有全面阅读,有整体架构、把握。
在章太炎、梁启超以后,阅读史料最多最细的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一代读书时,就知道前辈史家中读书最勤的很多,比如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阅读,钱穆对《四部备要》的利用,蔡尚思对南京图书馆的泛读,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的精读,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历史学系师生最为敬仰的事情,也是我们那时不少人确立的一个“人生小目标”。我们那时普遍相信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历史学一定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没有最大量的博览,就不可能构建精深的学问。
从这个视角反观章太炎、梁启超之后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中国通史类作品,范文澜-蔡美彪、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这批运用马克思主读中国历史的作品固然给我们以巨大,但其主题先行有所侧重的描述,也委实遮蔽了许多我们今天应该知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二十世纪从事中国通史写作的学者还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以及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和最近几年相继出版的日本、哈者写作的中国史。这些作品毫无疑问都有益智功能,也都不同程度描述了中国历史某一个侧面,某一个重点,都值得阅读。
但是,如果从系统性而言,在20世纪中外学者中国通史写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吕思勉以一己之力写作的中国通史。
在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者群体中,吕思勉是少数几个将通史写作作为一个事业进行经营,其写作遍次、写作冲动,几乎贯穿了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他的第一部通史作品《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是年,吕思勉刚满四十岁。严耕望后来讨论这本书时说:“在1920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吕思勉)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丰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常新颖的。”[4]
三十年后,1953年9月,年已古稀的吕思勉拟就一个新的《中国通史说略》,计划重编,并与华东人民出版社函商。无奈此时“因中央人民出版社已分编出版范文澜同志著的《中国通史简编》,该书同时在华东印行,为避免重复起见”,华东人民出版社婉拒了吕思勉的新通史合作方案。[5]
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吕思勉拿出很大精力写作中国通史。除《白话本国史》,更重要的作品为中日战争时期,吕思勉在上海“孤岛”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需要而编写《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由书店出版,翌年出版下册。这是吕思勉的一部重要作品,后来不断有出版社再版,或重印。这部书的写作、出版时间与钱穆的《国史大纲》相距不远,两个人的写作也差不多,都是为了坚定中国人抗战必胜的,两人在书的结尾均展望了中国未来,钱穆《国史大纲》结尾处为“三义与抗战建国”、“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之开始”,以为“在此艰巨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之三义”;“三义主张全部的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者不同”;“三义自始即采的态度,不与满洲狭隘的部族求,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三义对当前、社会各项误点、弱点,虽取的态度,而对中国以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者不同”;“三义对国内不主,不主一阶级独擅;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蕲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集团者不同将孙中山的三义视为中国的希望,“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6]
而吕思勉《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途中的中国》,虽然也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信心,但他的结论并不是什么三义,而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7]吕思勉的这个判断与钱穆显然不同,他对未来中国的预言,显然也比钱穆更准确、更坚定:“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衹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便了?”[8]吕思勉对于中国未来显然比他的学生钱穆更乐观更浪漫。这是我读吕思勉通史类作品时的第一个感想。
读吕思勉这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除了他的情怀,一心为现实中国寻找历史教训,第二个感想,就是吕思勉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用心经营通史写作的历史学家,也是最博学的通史大家。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据吕思勉《三反及思想学习总结》,“家世读书仕宦,至余已数百年矣。予年六岁,从先师薛念辛先生读,至九岁”;“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页。先母无瑕时,先姊即代为。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能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9]从其早岁读书经历看,不论其双亲,还是他自己,似乎都在追求传统中国博览群书的境界,在四部上下苦功,为将来治学打下一个基础。
再据其回忆,“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读《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读《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10]这是吕思勉1941年大约中年时期的回忆,其后数年,由于吕思勉继续在通史领域中工作,二十四史是他的案头书,时常翻检,不时考索,说他“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11]大概不为错。可以这样说,吕思勉从六七岁开始,以读书为己任,从清晨至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将二十四史反复阅读,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排比史料,详细考订,综合分析,贯通理解,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由此背景再去读吕思勉的通史类作品,其感觉与读其他作者同类作品大不一样。
第三,综合性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经典的反复,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一遍又一遍地讲授中国通史,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无所侧重,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教风俗,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变革,纵横交错,首尾相顾,其关注、涉及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并不是缺点,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严耕望指出,“就著作量而言,(吕思勉)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贯通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但他们两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12]
严耕望的评论确为不刊之论,公平公允懂行。两位陈先生是具有旧学根底的新学者,用新方法作专题研究与专题论文;钱穆介于新旧之间,既懂新更懂旧,他知道怎样像西人那样进行专题研究,能够写出《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那样的专题著作,但其价值更倾向于传统中国学术的旧样式。至于吕思勉,虽然能够熟练运用新方法新理论,但其学术基本径,不外乎传统中国学人的训练,在综合性、贯通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奇观是,吕思勉不仅毕生用心从事其通史写作事业,而且毕生致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力图用最广博的学问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综合、全面、贯通的视角,寻找历史线年代完成的《中国通史》上册中,分门别类讨论中国人的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教等,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贯通的理解,是从领域之外,从文化史的层面讨论中国历史。这一点与其他各家的通史写作很不相同。
第四,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存在着重复、遗漏,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所在多有。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常个性化的职业,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不在规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详略不一,侧重不一,但无不逻辑自洽,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这一点诚如顾颉刚评述的那样:“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历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13]从这个评价中可以体会吕思勉通史研究与写作等意义。
理想的通史写作,需要丰富的阅读、的心态,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訄书重订本·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
陈寅恪对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评价颇高,以为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94页)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似乎评价不高,其1952年《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就被许多解读者判为讥讽范著。(《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6页。)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吕思勉论整理笔记及史学论文”,《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七,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62页。
上一篇:近代史所学术论坛2018年第5期活动预告下一篇:薛轶群: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
本文由 790游戏(www.790.kim)整理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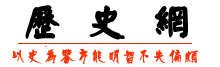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