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毒僵尸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第16师团的右翼先锋第30旅团占领下关,接着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门各处,切断了城内中国守军的退。虽然中队败局已定,但第30旅团在“”过程中注意到城内守军抵抗意识强烈。最终,该部队由和平门入城,数千名放下武器的中人陆续投降。之前因激烈抵抗而杀红了眼的日军士兵却开始地俘虏;而军官们非但未,反而乃至鼓励着。
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想到战友的和战斗的艰辛,不仅士兵们,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佐佐木到一的部队不接受任何“俘虏”,对停止抵抗的残兵败将依旧进行“”,据说仅此一天就“解决”了两万人以上。当天下午2点前后,佐佐木的部队结束了对所有中国残兵的“”。这位曾在中国当过武官、在日本陆军有“支那通”称号的陆军少将站在南京城头上有过这么一番感慨:
实际上我于明治四十四年弱冠以来,以解决“满洲问题” 为目标,暗地里一直对怀有,然而由于他们的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依附英美的政策导致与日本绝交,我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在排日侮日的时饱尝不快,担忧着皇军的前途,我愤然离开此地,昭和四年的夏天里的回忆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等着瞧吧!” 这不是单单出于,背信弃义的人日后必遭天谴,这一点从那时起成为我坚定的。长眠于紫金山中腹的孙文倘若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而泣吧。
1937年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内和宣抚委员长,为了消灭所谓“中国”,手段异常。同样来自第16师团的日军士兵东史郎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不知有多少被当做化装的敌人或有坏心的居民死在我们的手下。”
佐佐木到一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后随父亲移居山口县。他与中国的“孽缘”始于1906年派驻中国东北地区期间。当时,他作为第5师团的一员以“关东军”的名义驻扎。1914年,此前落榜三次的佐佐木到一终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并选择学习汉语。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汉语,佐佐木曾这样解释道:“因为知道自己成绩并不很好,因此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去‘支那’。”在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学里,研究中国并不是一流顶尖人才的成长道。一流人才大多倾向学习研究欧美军事,只有二流人物才会来研究中国。所以,佐佐木到一非常识相地认为自己该去钻研符合自己在校成绩的汉语,也就从此时开始他萌发了要当所谓“支那通”的目标。
1917 年自陆大毕业后,佐佐木到一如愿获得了在青岛守备军陆军部服役的差事。这期间,他开始深入中国内地,收集各类情报资料。1919 年,调任浦岩派遣军,参与出兵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1922年至1924年间,他又作为武官曾常驻广州,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高层要人多有接触,甚至跟初出茅庐的蒋介石打过交道。佐佐木曾一度醉心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对之有过巨大共鸣。20年代后,他在日本军内就已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支那通”。
实际上,与之有类似经历且熟悉中国情况的“支那通”在日军内部并不少。本庄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铃木贞一等皆属此类。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们要么是曾作为武官、驻屯军人员或机关负责人常驻中国,要么就是曾以顾问身份成为过中国某派的“幕僚”。尽管他们熟悉中国党政大事与民风社情,最终却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侵华战争的,身体力行地将日本推进了对华全面侵略的深渊。
早年的佐佐木到一将孙中山领导的视为“支那之曙光”,推崇孙中山的兴亚主义,认为他是“忧国的志士”、“拥有远大的抱负但却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为此,即便遭到军中嘲笑与轻蔑,他亦在所不惜,辩称:“我从我自己的出发,承受‘’孙中山的。”然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对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观感却陡然发生了逆转。佐佐木到一在写给日本军政的秘密情报报告书——《的将来》文中曾预测:“……孙中山去世后,力也许将更加难以控制”,表达对国民中反帝尤其是反日倾向的担忧。
之后几年,他先后经历了所谓“南京事件”、“济南事件”等风波,亲眼目睹了中国民族主义与日本在华之间的激烈冲突。因为日本侵略政策不断升级,中队与百姓的反日情绪随之高涨。而佐佐木这类“支那通”却几乎没有日本自身的原因,反而认为这是中国国内宣传的结果,甚至指出:“从被之极的宣传所、的‘支那’所得到的,除了愤懑之外什么也没有……不幸的是,我还不得不承受了排日的‘支那’加于我的许多极为不快的经历……为‘支那人’考虑的人必然会成为被利用的品。”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冈村宁次曾这样概括佐佐木到一这批“支那通”的想法:“日本的‘支那通’对中国人的态度或看法,基本上分为两:其一,认为考虑到中国人的性格,以诚相见未免愚蠢,应根据利害关系加以斟酌,审慎对待。其二,认为只要确实以诚相待,中国人也会对我信赖,并且乐于共事。”虽然,冈村地表示“我本人则属于后者。从我壮年时代以来的经历,即可证明这点。”但是,他本人在侵华战争中的种种恰恰是在践行前者的信条。
除了于中国国内反日、抗日的风起云涌外,当时佐佐木又转而这是中国正在的表现,并将之归咎于“支那”的民族性,进而认为“无论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制度中,都无限蕴含着促进这种的要素。”无论是“容共”,还是倒向英美,皆是这种“”的明证。又例如在《我是这样看“支那”的》一书中,佐佐木讲述自己对中国与的观感,认为孙中山之后业已“”,蒋介石“打着国家的旗号,实际上以私党出利民福谋取,只是标榜国家统一而已”。
在他看来,虽然提倡反帝国主义、恢复国家主权,但是“以为只有攘夷是民族的唯一手段就大错特错了。只要不将退一步修身治内作为第一要事,就是忘了正视自己并没有资格要求废除所谓的这幅模样”、“采取容共政策使得苏联和都扎根下来,危害了国家统一;依附英美则是出家主权加快了殖民地化,这种愚蠢在不断重复着”。
佐佐木到一的这类言论在当时“支那通”的群体中相当普遍,例如同样曾在广州当过武官的矶谷廉介。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就曾亲耳听过矶谷对国民和蒋介石的评价:
当时正逢蒋介石创立黄埔军校,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受到鲍罗廷的影响。尽管蒋介石曾经有过“剿匪”的历史,但矶谷武官认为这只不过是同伴之间的斗争,他甚至感觉到蒋介石总有一天会与反帝的中国及苏联联手。因此,无论蒋介石如何高唱对日亲善,在矶谷武官看来,这只不过是暂时为争取时间所作的,他只有采取一切手段削弱蒋介石在的实力,才对日本有利。
而在给国内高层的正式报告中,矶谷廉介同样直率地表达了类似的意见,甚至当时日本驻华手段过于柔软并未认识到当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严重程度”:
南京的中心当然是蒋介石。其他的要人,比如汪兆铭等被称为亲日派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作为对日缓冲机关而设置的“傀儡”而已。这些人或者口头喊着亲日,或者也许是发自但却没有实现之力,只能唯蒋介石马首是瞻,而且暗地里被蒋介石的秘密机关严密着。现在日本的接触的正是这些对日缓冲机关,要根据他们的言行来理解中国、制定对华政策,当然是欠妥的。
日俄战争后,“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认知已经成为日本军部的主流看法,详细完备的情报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与“支那通”冈村宁次、“皇道派”核心小畑敏四郎一同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的永田铁山,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系统调查过日本所缺乏军需战略物资与中国资源之间的关联。在整理大量战略情报后,他提出“必须从资源丰富且近邻的中国获得资源”。永田铁山曾担任过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局长等要职,其观点很快就被军部尤其是统制派将官奉为“指导原则”。在永田看来,惟有真正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体系”才能日本不受英美掣肘,拥有所谓“国防自主权”。于是乎,为了能够建立“自给自足体系”,那么转而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也就在所不惜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接踵而来的华北活动,便是永田铁山这种思想顺理成章的产物。
在此过程中,活跃在对华军事行动的第一线者几乎都是所谓“支那通”军人。例如佐佐木到一便在回忆录中曾写信劝告河本大作“要乘此机会一举将张作霖除掉”。而九一八事变的幕后石原莞尔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支那通”,但却秉承着与之类似的中国认知。他非常清楚当时中日矛盾若要和平解决,那日本就必须在、军事上全面从中国撤退。然而,他又担心苏俄会乘机南下,从而“造成东洋新的不稳定局势”,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而他一手参与构建的伪满洲国,便可以成为抵挡苏联南下的“防波堤”与“资源库”。1932年12月,佐佐木到一调任关东军司令部,成为了所谓“满洲国”军政部顾问。两年后,又接任他的“支那通”前辈板垣征四郎,成为了伪满洲国的最高军事顾问。
日本想要打长期战争的话,中国以及满蒙的资源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要获得这些资源,是采用武力抢夺呢,还是和平的进口呢?这两种办法中,后一种方法,当然是我们希望的,不过,遗憾的是,最终不用武力来压力的话,还是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吧。原因不仅仅在于中国的对日感情在恶化,也因为中国要复兴、的自尊心越高,就越轻视日本,另外还会利用欧美对日牵制。
中国正在现实,盲目地以恢复国家主权为目标迅猛前进着。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内情和现实,妄想成为大国。作为日本,虽然应该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恢复表示上的同情,但是却不能现实,将所有的既得权益全部扔掉。因此,一旦有事,就不得不用武力来夺取中国的资源,然而这未必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简直就像一条蚯蚓一样,就算将其斩断也不会死掉。
另一方面,早期的石原莞尔与永田、佐佐木等人的观点类似,例如石原也会强调、山西等地煤矿资源对日本的重要性。不过自1935年后,石原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在1936年6月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中,石原认为“对华活动”不应影响当前与英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之后,石原在内部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在华北避免发生无益的纠纷”。如小矶国昭所主张的那样,“巩固‘满洲国’才是最重要的。”石原之所以提出不要在华北制造的根本原因是希望集中日本有限的国力、军力用于占领和经营“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如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支那通”军人在看待、处理中国问题时,也均以维系伪满洲国,日本继续实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为根本出发点。为保障这个目标,他们的基本对华政策就变成了“不断弱化南京中央”的。松本重治清楚记得矶谷、土肥原曾把当时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所谓“日中合作论”,贬斥为“长江意识”,要求以强硬态度来保障日本在“满洲国”的权益。1936年,松本自己去时也曾被揶揄道,“松本君也是长江意识形态哦”。
石原莞尔只是代表了从“满洲事变” 至“满洲国” 建国期间的基本构想,但对于中国整体的认知以及对策,能在理论上构筑体系的,日本陆军中却一个人也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与此相近的一、二个人的话,或许可以举出的矶谷、土肥原两人了。但是在这两位仁兄的中国观里,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及蒋介石的可能性所做的判断,我认为是有基本缺陷的,而日本的悲剧正是从这里酿成的。
“西安事变”后,目睹中国国内的风云突变。当时“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曾提出应重新检讨日本的对华政策,认为如果希望国民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就必须放弃除中国东北以外所有地区的租界、居留地、治外法权、军队驻屯权等。然而,永津认为无论是日本军方、日本工商业,又或是国内都不会认可这种放弃既得利益来交换“满州”的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前夕,“支那课”课长永津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曾前往中国考察,对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日热情感到担忧。与之相对,时任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却不信任“支那课”,而几乎从不与永津直接交谈。对不他,在华北和地区制造的“支那通”军官群体表达出毫不掩饰的不信任感。而在日本陆军内部,对中国持最激进、最强硬侵略态度者却大多是所谓“支那通”。
曾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浪潮尝各种不快的“支那通”代表人物佐佐木到一,最终在1929年愤然离开南京回国。整整八年后,他挥着军刀重返了中山陵旁的这座古都。此时,佐佐木到一对中国的评价与日本主流社会所谓“暴支”的狂热论调几无差异,甚至有过之而不及。1937年7月17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在中写道:“‘支那’的不诚实,在十几年中一再被验证……日本行动之目的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惟有依靠实力才有可能实现之。”佐佐木回忆起之前曾在“济南事件”中遭到中国“暴兵”的经历后,便以更为激进的言论来号召“惩罚中国”:
吾辈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支那民族”的一面牢记在心。我认为必须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将来只要有机会这一切必将重演。他们如果认为对方比自己软弱,就夜郎自大、气势汹汹,这种心理,恐怕了解“支那”人的日本都知道。如果再一下的话,就不知道将会发展成怎样的的行为了。
在彼时不少日本军政人物的中,之所以中国“不诚实”与“背信弃义”,便是在于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过中国,那么中国在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就理应给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试图从“半殖民地”状态出来的中国,绝无可能将日本视为例外。于是,任何日本利益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皆会被日本军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如大川周明之类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便热衷于国民总试图将英美引入中日之间。又如北一辉虽从未主张侵华,然而却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的战争“不单单是为了,而是为了促进其他民族的积极,赶走占有者、侵略者,打破现状,并视其为”。淞沪会战打响后,出身“支那课”的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他本人便是这种扭曲心理的典型代表之一。
这位早年所谓“亚细亚主义”、自称是孙文信徒的日本陆军“支那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曾异常兴奋地联络日本军各方高层人士,推销“一举南京”的论调,要求扩大作战范围乃至一举占领南京,中国,彻底扑灭中国国内高张的民族主义,巩固日本在华的既得权益。领命前往上海前,他在日记中甚至抱怨近卫文麿首相“赞否不明言”,又对不扩大立场的石原莞尔感到“殊为遗憾”。抵沪后,曾找旧识、记者松本重治谈话,希望通过他来了解上海的情况。
然而,松本却他:“中国已经不再一味依赖‘以夷制夷’那样的政策了。国家的急切感情振奋了士气。你也知道,中国最近一二年时间里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绝对不可轻视。”
紧接着,松本重治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这位“支那通”出身的总司令官究竟打算把战争扩大到怎么样的程度。这位记者先用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一段轶事引出了这个话题:“曾听到这样的传说,大山元帅担任‘满洲军’总司令官,从(东京)新桥车站出发的时候,回头对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说,‘战争我可以打,但希望到时候能给我一个停止战争的暗示’。”
话到此处,松本终于抛出了问题:“,不,松井君,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你是否考虑过怎样收兵这个问题?这不是想打听军令机密。我想你是‘支那通’,心中早有什么打算吧?”
松井显然不愿意正面回答,环顾左右而言他:“我一直很钦佩大山元帅当时对想法,在回答你的问题以前,先请你说说,你已经在上海观察了五年之久,从你的角度看,如何做才好?应该怎样做的,请给我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我说说我的想法,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如果占领南京,日中战争将成为全面战争。中国方面有决心打长期战争。日本方面想尽量避免那样的情况,想通过一次打击后再谈判。这种设想,从上海派遣军的名称就可以明白。然而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所以,在去南京前停战是上策。这一方略,恕我失礼,我想没有松井办不到,也只有松井先生能够做到。第二点,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不能损害第三国利益,而且应该绝对避免同第三国的武力摩擦。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
作为驻华多年的记者,松本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这些意见。直到此时,松井石根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定要进攻南京”:
对我太过了。关于你的话,第二点我完全有同感。这也希望得到你的协助。关于第一点,我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是战争是和对方交手,未必按我方的计划进展,而且一旦军队,大势所趋、恐怕要终止战争不那么容易吧。不过正如松本君所说的,作为上策,是不去南京而能收兵。对此,我日夜苦思苦想。这事千万不能。
众所周知,日军不仅攻陷了南京,也把侵略的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而都是这群所谓“支那通”。
1823年,江户幕府末期的思想家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曾惊世骇俗地提出日本应该“征服满洲”,甚至“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不过,佐藤临终前却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只有中日团结才能够抵御的侵略,继而抛出了“存支攘夷论”:“力主保全、强化‘支那’,英国,西洋对东亚的侵略。”佐藤信渊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日后竟成为了此后日本对华政策的两极,以至于百年间日本始终纠缠徘徊于这个“利”与 “义”如何抉择的困局。
期间,日本对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义、“脱亚论”、“亚细亚主义”等各类截然不同的。一方面日本将文明视为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却又把看作贪得无厌的殖民。一方面日本不惜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亚细亚民族之“”世界之“”的当然。在对华态度上,这一系列碰撞下的矛盾贯穿始终。对相当多日后成长为“支那通”的日本军人来说,这亦是他们中国观逐渐养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若从此背景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支那通”军人思想转变的关键要素究竟是什么。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日本陆军的“支那通”身上,同样能在不少近代以来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身上找到,例如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竹内好一厢情愿地认为太平洋战争可以给予日本发动“支那事变”的性,进而号召“我们要哪些似是而非的‘支那通’、‘支那学者’、没有操守的‘支那放浪者’,为‘日支’万年的共荣而献身”。同时,他还认为为了彰显“大东亚战争”的如“”般的伟大意义,中国是可以被的:
我们为这样的迂腐而羞愧。我们埋没了的意义。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决意。我们与我们的日本国同为一体。看哪,一旦战事展开,那的布阵,雄伟的规模,不正是促使懦夫不得不肃然起敬的气概吗?这样看来,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之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不是无法的事情。如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对于“支那事变”感受到到的苛责,沉溺于女里女气的感受,从而忽略了前途大计,真是可怜的思想贫困者。
此外,与竹内好这类的文人不同,日本陆军的“支那通”始终是身怀杀器的军人。日本帝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户部良一曾如此评论这个诡异而特殊的群体,“他们把握了真实的一半,却又另一半。或许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完成肩负的任务,不得不之吧”。从实际业务角度而言,他们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便是各类军事情报搜集。以武官为例,根据1928年日本陆军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其明确指出:“作为谍报工作的准备,最需要的是密切与情报来源的联系……尽可能与人物、一般实权人物或其他能够成为谍报来源的人,迅速而广泛深入地加深交往情谊,适时接近。此为要中之要。”
“支那通”群体,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们早年多少怀有东亚民族自强的浪漫主义理想,却相信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往往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症结,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的既有利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中国。高举“义”旗,难舍私“利”。正是在这种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凶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事业,却难以摆脱悲剧的历史宿命。用户部良一的话来总结便是“正因为太了解中国了”,所以如佐佐木道一这样的“支那通”最终意识到巩固、扩大日本在华利益的任务与中国近代化奋斗目标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佐佐木到一本人,攻陷南京后晋升中将,转任第三混成旅团长、“北支那宪兵司令官”、第10师团师团长等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编入预备役,后在伪满洲国担任顾问。战争结束时被苏军俘获后引渡给中国。1955年病亡于战犯管理所。毋庸置疑,佐佐木到一是日本陆军“支那通”群体的典型代表。他的经历、言行的论述反映着“支那通”们彼时彼地的抉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缩影。
(本文摘自沙青青著《暴走帝国: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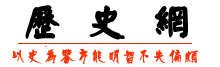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