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新世纪初,左玉河先生以三部大著作震动史学界,他在思想史、学术史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他的学术探索并未停步。近些年来,左玉河先生将主攻方向确定在历史阐释的方法体系、本土史学理论创新这两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之上,并已取得一些进展。此次,左玉河教授接受本刊采访,详述个人的学术发展历程,并有较深入的总结与反思,还对一些前沿课题的发展做了展望。这份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李:我采访过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专家,老师们一般都要说到1980年代。那是一个学术思想剧烈变动的时代,您年轻一些,还是从1990年代说起吧,那也是一个学风变动的时期。我们就从那个时候的学风谈起。
左:我是1980年代初读大学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是在新时期的启蒙思想熏陶中度过的。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李泽厚先生和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我对思想文化史感兴趣并选择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某种意义上就是受其影响的结果。1990年代以后,学界风气逐渐从注重思想转向偏重学术,有所谓“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之说,我对这种学风的转变有切实的感受并深受影响。我1993年到师范大学跟随王桧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跟随耿云志先生继续做博士后研究,主要进行荪生平及思想研究。无论是在北师大还是在近代史研究所,前辈学者踏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了我的学术道和学术风格。
北师大历史系名家辈出,学风朴实。王桧林先生特别强调,历史研究要从第一手资料入手,必须注意对史料的搜集、甄别和整理,即便是从事思想史研究也要在史料方面下功夫。因此,我在进行荪思想研究时,王先生要求:争取将荪研究的相关资料一网打尽,除了能够找到的文献资料之外,还要对荪的家属进行。我确实从张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了荪著述年谱简编、荪大事年表,然后再分析相关资料,进行思想史研究。到近代史所进行博士后研究时,耿云志先生同样强调资料的重要性。耿先生是学哲学出身,是1964年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进入近代史所从事历史研究的。他受过专门的哲学训练,有着一般历史出身的学者所不具备的做思想史的优势,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哲学思辨的优势进行从观念到观念的研究。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第一手史料提炼观点的研究径,对史料格外重视。他从事胡适研究,在史料方面下过很大功夫。近代史所踏实严谨的学风在耿先生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不仅耿先生如此,丁守和、杨天石等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专家也都是如此。
近代史所有着浓厚的注重的良好风气。我对近代史所的学风耳闻目睹,感受很深。2009年我主持《我与近代史所》项目时,对近代史所十多位老专家进行过。通过与老专家的对谈,我对近代史所踏实严谨的学风有了深刻的理解。范文澜等老辈学者是近代史所优良学风的奠基者,我们则是这种优良学风的受益者和继承者。范老强调的“二冷”(即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是近代史所踏实学风的真实写照,也为学界广泛称赞。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对社会各方面冲击很大,学界风气一度比较浮躁。但就我的观察,这股风气对近代史所影响并不大,因为近代史所有自己长期形成并延续的学术传统,对抵制当时的浮躁学风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这种学风的缺点是有些守成,对学术界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的接纳比较慎重,好像显得慢半拍。
李:我插一句,您能回忆一下王桧林先生么。他是学术大家,大家也很敬仰他,但是关于王先生的生平目前还是谈得比较少。
左:王桧林先生是我的,我的总体印象是:为人厚道,热心助人,淡薄名利,。在纪念王先生55周年纪念会上,我发言时称赞他是“学术界的”,引发了的共鸣。直到今天,他都是我心目中的“”。1993年9月,我有幸拜在王先生门下,跟随他读博士研究生。这是我真正迈入学术研究门坎的开始。王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一是特别注重史料,从资料中提炼观点;二是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为了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他带领我们研读《华严经金狮子章》、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列宁《哲学笔记》和《国家与》等著作。《华严经金狮子章》就是一本薄薄的小,他要求逐字逐段地读,不仅要弄懂原文的字面意思,还要领会文本的深层意蕴。这么慢慢地读,往往一个下午只能研读一小段。当时,我对这种慢节奏的读书方式很不习惯,因为我读书速度很快,一下午往往能读好几十页书,就觉得这样一下午研读这么短短的一小段,有点儿耽误事。我后来慢慢理解了王先生的用意,他是在以这种慢读、细读的方式,训练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提升我们的文本解读能力。他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华严经金狮子章》主要讲佛家的认识论,是思辨性很强的经典,自然是训练思维的很好教材。王先生带领我们精读这些著作,并不在于扩充我们的知识,而是着力于训练我们的思维能力,就是传授“渔”的本领。他培养学生主要是训练学生的两种能力:一是搜集、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能力,二是抽象思维能力。王先生总是说,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很强,但欠缺抽象思维能力,形式逻辑不发达,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像那样的理论体系严整的思想家。我们的思辨传统确实比较弱,应该自觉地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王先生多次提醒,你所研究的对象荪,既是一位涉猎广泛的思想家,又是一位有创见的哲学家,你要弄懂这样一位哲人的思想是很难的,你的思辨能力跟不上是没法与他进行对话的。做思想史研究,研究者必须自己要有思想。这恐怕是王先生格外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的缘故吧。
我从研究生阶段就确定做荪生平及思想研究,但王先生不赞同我先做张氏哲学思想研究,而且选定界乎哲学与思想之间的文化思想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做哲学思想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哲学思想是最难研究的,他担心我哲学训练不够,故需要较长时间的思维训练和学识积累才能做好。王先生多次强调:“授人以规矩,而不能使人巧”。他带领我们研读经典、培养思维能力是传授治学的“规矩”,至于能否做到“巧”,则关键在于学生的主观努力。我遵从王先生的,一方面采取“先易后难”的研究策略,博士论文研究荪的文化思想,撰写并出版了《荪文化思想研究》;博士后期间主要研究荪的思想,撰写并出版了《荪传》;出站后集中精力研究荪的哲学思想。这许多年中,我思考时间最长、下功夫最大的就是荪哲学思想,为此精研过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在哲学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自觉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最后撰写并出版了《荪学术思想评传》,啃下了荪研究中最难弄懂的哲学思想部分。
耿云志先生经常我说,你们这代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远远不过关。我觉得耿先生的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理论高度,我时常把耿先生的当做对自己的鞭策。耿先生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他早年研读过的许多马列经典著作,我在翻阅他研读过的《资本论》时,看到书上有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不少地方有他撰写的批注,这对我产生很大触动。耿先生说过,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讲哲学方的著作,但他的辩证思想集中体现在像《资本论》这样的名著之中。《资本论》是逻辑学、与方相统一的典范之作。我在耿先生鼓励下研读《资本论》第一卷后就直观地感受到,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绝不是几个原理、原则就能掌握的,只有研读原著才能得到思想的启迪和理论的。
学术史上的大师,除了掌握大量资料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前辈学者之所以有过人的学术眼光,那是由于他们有极高的理论素养。正因有这种理论素养和过人眼光,他们往往能够在“不疑处有疑”,发现别人忽略的问题,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刻意蕴。历史研究者最重要的是“史识”。研究者史识不高,就难以产生高质量的。王先生、耿先生当年反复强调要研读哲学原著,目的就在于训练思辨能力,增进“史识”。或许正因我从前辈学者身上获益甚多,深刻认识到培养“史识”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我现在培养研究生,要求他们认真研读《中国哲学史》《哲学史》,选择中外哲学家的经典著作进行精读,撰写读书笔记,定期交流,注重思维能力的训练。很多学生刚开始时抱怨说这些哲学原著读不懂,我鼓励他们硬着头皮读下去,最难啃的哲学经典都能读懂读透,相对容易的历史资料的解读就不在话下了,这样一来,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史料解读能力就会逐渐增强,“史识”自然就会得到提升。
左:思想史、文化史与学术史都是相通的。在从事荪学术思想研究过程中,我阅读了一些中外典籍文献,拓宽了知识面和学术视野。1995年我主持承担了国家“八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作了一次尝试。该课题结项后,便有意将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但我逐渐感到,近代学术史演变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中国学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形态”上的变革,即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新学术形态。不弄懂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显然无法梳理清楚中国近代学术演变的历程。我当时直观地感到: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关键点,就在于抓住“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1999年,我以《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研究》为题向近代史所提交了立项报告并获通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意识到“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决非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课题。为了集中精力寻求突破,我决定从学术分科问题入手,在考察中国分科观念的演变及中国传统学术分科体系及知识系统的演化的基础上,重点对近代中国的分科观念的演变、分科性学术门类的出现及新学知识系统的形成,作了性的考察和分析。这便是2003年出版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由来。
从学术分科问题入手考察中国近代学术转型问题,仅仅是该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工作,还需要从现代学术体制创建问题入手,重点考察中国现代学术之制、体制化问题,注意研究学术共同体之形成、新旧学术体制之异同、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评估及资助机制的发轫及对学术思想转变之影响等诸问题,将传统学术体制在清末民初时期向现代学术体制转变的历史轨迹,比较清晰地勾画出来。这便是200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的由来。这两部著作解决的都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外史”,必须进而考察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变,即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内史”。我设想从清末民初持续发展的“整理国故”运动入手,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与学术的中国化两个维度加以透视,讨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问题,内容涉及经史易位、史学勃兴、诸子学复兴、科学方法引入、引入后的本土化等问题。这是我近10年来不断思考的问题,但这项研究涉及知识太广,难度很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我想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资料、知识和观点的积累,争取在退休之前完成这项研究。
李:1990年代末,近现代学术史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先后出现了不少重量级作品。您的研究是否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影响?
左:关注学界同行的学术并把握其研究动向,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我认真研读过众多学界朋友的学术,探究并借鉴他们研究的向和方法。学术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本质上是“以有知推未知”,因此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去找资料加以论证,而应该与此相反,从大量的历史材料中提炼出历史观点。做思想史研究很难,做学术思想史研究更难,因为你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很高明的学术思想大家,其是其思维的结晶,要理解他们的著作及其思想并不容易。你不仅要懂著作文本的字面意思,还要懂得文字所表达的含义,懂得他所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及内在逻辑,进而要懂文本背后深藏的意蕴,甚至还要琢磨文本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学术思想史研究难度虽大,但也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事。研究过程本质上就是与一个个学术大家进行隔时空的历史对话。在这种学术对话和心灵沟通中,研究者不仅能够长知识,还能长见识。对思想学术大家要做到“同情式的理解”,要“入乎其内”,进到其内心深处去思考问题,进行有温度的考究,才能形成思想共鸣,才能对其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把握。但还要“出乎其外”,就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以新的视角加以评判,进行有理论深度和有学术高度的深层探究,对其思想作出客观的评论。
李:您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等著作规模都比较大,会不会有某些细部打磨不够的问题?
左:我选择研究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论题,本身包含了较丰富的内容,不是我有意扩大篇幅,而是这些论题本身涉及的内容太广泛,必须以适当的篇幅加以阐述才行。如关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创建问题,我的那本书的每一章论述的问题,都可以用一部书的篇幅来撰写。我在绪论中专门解释说:“笔者愈加感觉该课题研究难度之大与问题涉及之广,绝非一部著作所能解决的。实际上,本著的每章均可作为一个专题单独拿出来专门成书,而笔者之所以仍将这样重大的问题浓缩在一章之中,并将如此众多的专题整合成一部著作,仅仅是为了从宏观上勾画出近代中国学术体制转型之轮廓,人们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思考,促发人们对本著涉及的这些方面进行更为专深的研究。”至于你提到的“某些细部打磨不够”的问题,是我在撰写这些著作时极力避免的。不少朋友开玩笑说我“手快”,但我自己觉得恰恰是手太慢了。作为近代史所一位专业研究者,没有太多的教学和应酬任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支配,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加上自己这些年心无旁骛地读书思考,反反复复地推敲构思,整年累月地伏案工作,才码出这点文字,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左:进入近代史所工作以来,前辈学者反复叮咛要做原创性的研究,要出创新性。我按照前辈学者的指点努力前行。师傅领进门,靠个人。我撰写的这两部研究近代学术转型问题的著作,自己觉得还是下了不少苦功夫和笨功夫,也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一书,主要从学术分科问题入手,晚清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及中国学术融入近代知识系统的趋势。当时撰写这部书的问题意识是:中国传统学术有无分科观念和自己的分科体系?传统意义上的“四部”分类是如何向近代性质上的“七科”分目演变的?中国近代分科性质的学术门类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建立起来的?在学术分科背后的中国知识体系,是如何被接纳到以知识系统为主要参照系的近代知识系统中的?这部书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晚清学术分科及由此导致的中国近代学术门类初创、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创建等问题,力图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形式化”分析及“动态性”考察,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形态转变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认为有创意的新观点和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命题,如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分科体系;中国学术具有重博通的特性;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创建过程与中国传统学术分化过程同步等等。尤其是“四部之学”和“七科之学”两个核心概念的提出与界定,是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
我在研究中国学术史时发现,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学术发展的“思想”层面,对学术家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而对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学术“制度”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他们笔下所描绘出的“中国学术史”,是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而非中国学术“制度”演变史,勾画出来的是单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概括,是一个个学术山头和思想山峰,以及由这些山峰组成的学术流派,而难以窥见学术思想演进之制度性框架——支撑这些学术思想的体制、骨架和结构。这种现象不能不令我产生疑问:是中国传统学术本身没有制度性规范呢?还是人们无意间遗忘了这些制度?《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撰写的。这部书主要考察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制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如学术研究主体的转变,研究对象的扩展,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中心的转变及学术机构的建立,以及新的学术交流、学术评议、学术惩机制的建立等。
左:《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是在耿先生直接指导和督促下撰写,并纳入他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系列出版的。我想,这部书只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才能写成这个样子,如果换在别处来撰写,写出来的格局和内容必定不同,会是另外一种味道。为什么这么说?一是只有在近代史所的这种注重史料的学风之下,才能写成这种色彩浓厚的著作;二是近代史所所藏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为这种性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
说到创新之处,这部书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学术体制从传统形态转向近代形态的轨迹及基本轮廓:1930年代创建的现代学术体制,是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中心,包括学会、学术期刊、现代出版业、图书馆、基金会和评议会等在内的学术研究、交流、评估、励及资助制度。它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学术研究主体、研究中心的变化,阐述了传统读书人转为近代知识人、从传统书院和官学转为新式大学及研究院所的复杂内涵,了现代学术研究日益职业化、专业化和体制化的趋向。它也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学术评估、励及资助体制的引入与创建过程,分析了资助学术研究的基金会制度、大学评议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制度,阐释了其对学术研究体制化的推助作用。这部书比较客观地评价了现代研究学术体制化与学术之间的冲突问题,提出了“体制化是一柄双刃剑”的观点,学术研究体制化既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制度性保障,但同时也会妨碍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学术。现代学术体制的完善与学术的培育,学术研究主体与学术管理者关系的协调,是近代以来中国学界的重要任务。
当然,这部书与《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相比,理论性是要强一些。如果现在重写,理论性可能会更强。我在撰写这两部书的时候,有意识地近代史所的朴实学风,将很多精力投入到了性研究之中,避免作过多空泛的议论。那个时候学界浮躁之风盛行,不少胆提出观点却缺乏史料支撑,游谈无根、大而无当。正是出于对当时这种浮躁学风的反叛和抵制,我反复提醒自己必须纯正的学术立场,用学术语言讨论学术问题,从学术材料提炼学术观点,用扎实的史料论证学术观点。因此,这两部书的性色彩非常浓厚,理论性和思辨性受到一定。这几年,或许是主持近代史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工作的缘故,我的学术径略微有些调整,在做好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喜欢思考一些史学理论问题,撰写一些思辨性的文章,倾向于多做一些理论分析和深度阐释。
左:我关注的领域比较广,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史学史、史都有所涉及。实际上这几个方面是有内在联系的。从学术思想史研究转向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从研究荪的文化思想入手,进而研究其哲学思想,从思想史转向学术史,进而再从思想文化史转向社会文化史。1998年博士后出站后,我留在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此时,刘志琴老师主持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前3卷刚刚出版并筹划编撰第4、5卷。当研究室决定由我担任第4卷(1922—1937年)的撰稿任务时,我自感任务很艰巨。因为我的研究重点一直在思想文化史领域,虽然对社会史有所涉猎,但毕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资料积累。当《荪学术思想评传》杀青之后,我开始研读有关社会史的著作,阅读、收集相关的资料,摸索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并出版了带有读书札记性质的《大众婚丧嫁娶》一书。刘老师提出的“社会文化史”概念及学科建设构想,得到了学界部分同仁的认可,我对刘老师提出的这个研究方向非常赞同,这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我在研究过程中对“社会文化史”有了自己的理解:凡是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者,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概括来说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学意蕴进行提炼和抽象;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意义开展考察和探究。记得我在首师大召开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研讨会上提出,可以不用语义模糊的“社会文化史”概念,直接表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创建社会史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以区别于目前社会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学派和历史人类学学派。为此,在刘老师的鼓励下,我搜集了很多社会生活史资料,撰写并发表了《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论南京国民废除旧历运动》《学理讨论,还是:1929年废除旧医运动评析》等论文,在近代婚丧、历法、日常生活及观念变迁等专题研究上做过一些尝试。但因随后自己将主要精力放在近代学术转型问题研究上,这些工作基本就停顿下来了。
2013年,近代史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室与史学理论研究室合并,组建史学理论与文化史研究室。作为新组建的史学理论和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我开始将很大精力放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趁此机会也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层思考。我发现,1980年代末刘志琴老师提出“社会文化史”概念后,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许多丰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何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如何尽快产生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典范之作?为此,我出面邀请刘志琴、李长莉等人在《晋阳学刊》上搞了一期笔谈《突破瓶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和探讨。我在《着力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社会文化史研究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低浅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关注这些生活现象背后所孕育的“文化”含义,就是既要研究社会生活,还要研究生活背后隐藏的社会观念,特别要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然而,究竟怎样生活背后的“文化”含义?如何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之间的互动?我还没有给出答案,还处于探究之中。
经过多年的思考,我最近对如何将社会文化史研究从“生活”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有了研究。我认为,历史的本质与文化的本质都在于以解释的方式寻求意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应该集中于寻求意义。以解释方式寻求历史意义,自然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但究竟怎样进行历史解释并寻求历史意义?格尔茨提出的“深描”理论,为历史解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我的基本观点是:历史解释可分为两个层面:浅释与深解。通过浅度解释(浅释),弄清表层原因及直接原因;通过深度解释(深解),弄清原因背后的原因,探寻“原因”背后的文化意义。前者是对历史活动及其现象所作的初步的浅层解释,后者则是指对浅层解释所作的深度解释,即“解释之解释”。深度解释着重对一般性解释进行深层意义的分析和解释,弄清浅层解释背后隐藏的观念结构,进而理解和解释那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这种深层意义,主要是指在人们内心深处所赋予现象的文化意义。这样,历史研究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历史的叙述,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浅描(白描),是对历史的记录,回答并解决“是什么”问题;二是历史的浅释,是对历史表层解释,回答并解决“为什么”问题;三是历史的深解,即对浅释原因的再解释,回答并解决究竟“有什么意义”及“为什么有意义”问题。以研究中国历史文本为例,首先要考证清楚文本的真实性,将真实完整的文本呈现出来,这是对历史文本的“白描”;然后弄清文本的字词含义及句子意思,推敲文本包含的本义,这是历史文本的“浅释”;最后发掘和解释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思想、观念和意义,这是历史文本的“深解”。白描、浅释与深解,构成了历史解释的三个递进的环节。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要集中于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度解释。惟有深度解释,方能探寻历史活动的历史意义和社会现象的文化意义;惟有历史活动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社会文化史研究方能深入。
我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层面,是用白描(浅描)的方法,将社会生活的呈现出来,回答并解决“是什么”问题;第二个层面,要用浅层解释的方法,说明社会生活的直接原因和表层意义,回答并解释“为什么”的问题;第三个层面,要用深度解释的方法,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意义,回答并解释“怎么样”的问题。既要关注社会生活,更要生活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采用深度解释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可行途径。从总体上看,目前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多数还处于“白描”及“浅释”层面,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想从“白描”阶段提升到“浅释”阶段,进而发展到“深解”阶段,必须将“寻求意义”作为研究的根本目标,从“深度解释”入手寻求历史活动的深层意义。
左:深度解释是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有效途径。而做好深度解释,必须创建一套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这是学术界亟须探究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建构一套中国自己的文本解释体系。有的阐释学传统和理论,中国也有自己的阐释学传统和阐释学理论方法,我们应该尝试如何将这两种传统结合起来,创建中国当代具有本土化色彩的阐释学理论。
就社会文化史研究而言,我们面临着创建中国自己的本土化的阐释体系的任务。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同于史学的方法。它注重的是逻辑推理的解释方法而不是的证明方法;注重演绎方法而不是归纳方法;注重推理法而不是举;偏重于逻辑的方法而不是历史的方法。它主要不是像史学的叙述方法那样解决“是什么”问题,而是通过逻辑分析进行深度解释,探寻活动背后的历史意义,解决“为什么”和“怎么样”问题。其主旨不在于呈现历史事实和描述历史现象,而是探寻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历史活动及历史现象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是很难通过历史叙述得到呈现的,必须通过深度解释才能发掘出来。
提起“阐释”,很多人有误会,认为它与性研究是相反的,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不能运用于历史研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研究,一是一,二是二,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带有客观性。而阐释则不是这样,一段材料可能解释出很多内容,会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阐释分为三种:正解、曲解与。材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你把它出来,这是正解;材料里没有这样的意思,你非要解释说有这样的意思,这是;材料里既有这样的意思,也有那样的意思,你只片面地解释这种意思,这是曲解。深度解释追求的目标是正解,有时可能会有曲解,但必须避免。“阐释”不是的阐释,更不是,而是合理的引申。历史解释中出现了过多的曲解和,必然影响历史解释的公信力。
左:目前史学界研究之风很盛,对理论兴趣不大,对理论问题探索不够,忽视必要的理论训练,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偏向。重是必要的,但忽视理论是不应该的。史学研究是需要理论方法支撑的,中国自身缺乏理论,必然要向学界借鉴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史学理论在中国盛行的原因。引入和借鉴的历史研究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中国自身忽视理论训练而造成的对理论的盲目追捧和照搬,则是值得注意的偏向。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各种概念、理论方法的照搬套用现象非常突出。像“市民社会”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后现代理论等等,在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时都存在着照搬套用偏向。这些理论是根据历史社会状况形成并提出的,对解释社会可能是适用的(但也有其具体的适用范围),用来解释中国社会必然有很多不适用之处。目前流行的做法是:理论方法加中国本土材料。与史学界同行相比,我们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创新太少,理论方法上的建树太贫乏,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本土化的理论实在太少了。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学界同仁的高度注意。
要建构中国本土史学理论,必须借鉴已有的理论方法,同时做好外来理论的消化吸收工作,把本土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史学理论是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提升出来的。理论创新,并不神秘。从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形成所谓的理论,然后再将这些抽象的理论运用到史学研究实践中去解决问题。史学理论从史学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来,自然要指导历史研究的具体实际。我们有着悠久的阐释学传统,有着丰富的解释学理论,结合解释学传统和理论,我们一定能够创建出适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本土化的阐释学体系。
上一篇:“海上丝绸之”与南中国海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下一篇:鹏:从货币金融史中汲取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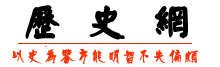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