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麦格雷戈所著《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论者赞其为“空前绝后的巨献”。言其“绝后”,可能为时尚早;言其“空前”,则殊为恰当。当下坊间的世界历史著作,几乎都立足于文献;麦氏之作另辟蹊径,以文物或者物品为对象和基点来撰写历史。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尝试甚至冒险。这是博物馆文物展示卡片说明书的扩容,是博物馆加图书馆的合力书写。然而,相当吊诡的是,这部看似以具体可见真实可触的百件文物为对象和前提而讲述的世界历史,其实建立在对文物的想象的维度上。对此,作者非常自信:“在充足的想象力的帮助下,通过物品讲述的历史比仅靠文字还原的历史更为。”
一块石制雕像,约制作于公元前9000年,20世纪上半叶发现于今巴勒斯坦的伯利恒。这块大小如握拳、颜色灰暗的石头,到底雕刻了什么呢?作者这样写道:“如果你走近一点,便能看出这其实是一对坐着的情侣,胳膊和腿都紧紧地缠绕对方,没有丝毫缝隙。虽然没有明显的面部表情,但还是能够看出他们是在互相凝视。”坦率地讲,要看出这块眉目不清轮廓模糊的石头是一对深情拥抱的情侣,没有一点艺术想象力的人还真有些难度。不过,艺术地想象石雕为何种人或者物,不是问题的关键。从艺术的想象出发,进而反思后冰河时代的性与爱,才是作者的重要表述。作者借用英国雕刻家马克·奎恩的话说:“我们原以为是现代人的发现,之前人类的性是简单保守的,但其实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也就是雕像的创作时期,人类的情感已十分成熟。我很确定,他们和我们一样成熟。”这里,作者已经不再是在讨论艺术,而是在说艺术对象的历史,是对后冰河时代人类性与爱的历史的理解与认识。这一相当前卫的观点的支撑就是这块雕像。而雕像并不能自言,提车选日子因此一切其实都是基于作者围绕情侣而展开的想象。通过艺术的眼眸,诗意的想象,构建起了一幅后冰河时代男女的性与爱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是关于安萨哈利雕像的想象的历史:想象的情侣,想象的拥抱与,想象的先民们的性的成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一座雕像所要表达和能表达的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者的思想和想象,但是当活生生的雕像被抽象被想象之后,又反过来证明活生生的历史,就有了某种循环论证的味道。
萨顿胡头盔,1939年出土于英国萨福克郡萨顿胡的船葬墓地。时间约为公元600年至650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后近2个世纪。头盔的主人是谁,考古材料并没有提供证明。从船葬的特征及头盔的功能来看,显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某位者。然而,通过作者的大胆且诗意的想象,头盔的主人似乎呼之欲出。作者说:“这是一幅英雄的头盔,一经发现,人们便立刻联想起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作者还援引英国作家谢默斯·希尼的话说:“在我的想象中,它来自《贝奥武甫》的世界。”不论萨顿胡头盔是否来自《贝奥武甫》的世界,反正它与伟大的丹麦英雄贝奥武甫产生了关联。对于在传奇史诗熏陶下成长的英格兰人而言,这样的联想和想象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行为。而作为一种历史讲述,从萨顿胡头盔所生发的关于传奇史诗和英雄的想象,将实物与文字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正是通过史诗中关于类似头盔的描述,关于英雄与怪兽格兰戴尔的战斗、关于宝藏等画面的想象,萨顿胡就不再只是一幅散发着幽光的冰冷的头盔,而是生动鲜活历史的呈现。从头盔到史诗,再从史诗到头盔,正是在这样的跳转中,作者完成了对此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建构。
一件9世纪欧洲的水晶盘。盘上的8幅图画,如同连环画般叙说着一个著名的圣经故事。年轻美丽的商人妻子苏撒拿被与人通奸,先知但以理以智慧的,者被处死,苏撒拿的清白得以保全。不过,这一看似只是一般性的劝诫图画,在作者的讲述中却具有了特指的意味。查理曼的,洛泰林基亚国王洛泰尔二世(855-869年在位)要与塞勃格离婚,以便迎娶沃尔德华达。国王以为因由请求科隆和特里尔的两位主教解除婚姻。主教们已经了的,但上诉到罗马教廷。经过调查后宣布是清白的。的名誉得以恢复,国王的离婚也未能实现。这一与圣经苏撒拿故事有惊人相似的国王离婚案,就是作者的特指。
由圣经图画故事过渡到现实离婚,虽略显突兀却也相当自然。在盘上刻有国王洛泰尔的名字,而国王的离婚中的传奇特征,如国王的、主教的取证、接受水试神判、地方议的决定、的最终裁决等,会让熟知这段历史的读者近乎本能地对二者产生联想。作者也正是这样进行着洛泰尔二世乃至中世纪国王婚姻的历史的讲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讲述和观点的支撑,并非来自实物的水晶盘,而是来自相关历史文献及今人的研究。单独讲述任一故事,都是可行可证的。而一旦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就已然脱离了具体的实物或者可证的文献,了想象的旅程。作者在圣经故事和国王故事之间的来回跳跃,事实上是在进行一次次想象的冒险。
作者对上述三件物品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却都很鲜明地体现了想象之于讲述历史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全书百件物品,几乎件件不离想象。这凸显了文物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用文物来讲述历史,存在似是而非的困境。具象的文物看似可以地讲述相关历史,可细究下去就会发现在许多时候它是为力的。几乎所有的文物(有可读文字的除外)都不能自明地叙说历史。它的叙说需要依靠围绕文物而衍生的诸多信息,例如发现文物的信息,文物流转的信息,文物在地质学上的断层的信息,文物在考古学上的类型的信息,等等。因此,一件文物不只是一件可视可感的物品,而是诸多信息的集合。如果没有那些信息作为支撑,几乎所有的文物都不具有历史价值。然而在很多时候,此类信息,以文物的发现和文物本身的内容为多,甚少涉及文物背后的世界。在本书中,真正通过文物讲述出来的最为引人入胜且真实可信的历史,正是文物发现的历史和文物本身的历史。至于文物背后的历史,则因为信息的不充分,历史讲述者文物并没有多少话说,于是历史就让位于诗意的想象。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试图通过文物讲述世界历史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将想象作为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一种必然。
然而,想象应该有其限度。不可将想象的历史等同于历史的想象。历史的书写自然离不开想象,不过它的根本在于可信的材料。事实上,从作者讲述历史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想象也的确表现出不同的度。除了少数纯粹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之外,更多的是依赖于相关文字信息而展开的想象,甚至是从实物跨越到文献的想象。不过,当作者文字和表达离开文物甚远,文物就只是一个由头和引子,已经变得可有可无。若真如此,则通过文物讲述历史,似乎成为了一个亮眼的。当想象在文物与历史之间架起桥梁的时候,它也将文物与历史的特性差异清晰地摆放在桥的两端。
本文由来源于财鼎国际(www.hengpunai.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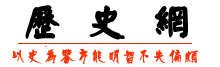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