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的历史学家孙隆基出现在宾馆咖啡厅时,看上去老了不少,走很慢,面容疲惫,没了两年前那股精气神。这种状态的变化,可能与年龄以及生活中发生的变故有关,可能是因为过紧的行程安排,但或许更可能是他把全副身心都倾注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鸿篇巨制的《新世界史》的写作中。
已经出到第二卷的《新世界史》,原计划是写三卷,但孙隆基承认,随着写作的进展,现在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写到何时才会终结,按目前的计划,至少还要写两卷。这部大作,几乎重构了近一万年的世界历史,需要调度海量的史料,理清太多错综复杂的脉络。这通常是像“世界史”、“剑桥世界史”一样,需要调动十几乃至几十位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学者分工合作的大工程。难以想象,这项工作可以由七十出头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在孙隆基之前,华人学者也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一位熟悉他的出版编辑告诉记者,对严谨的孙隆基来说,这项工作进行得很不轻松,但“他有一个动力一直做下去,他希望把这件事做完”。
大概是埋头书堆太长时间,脑中时刻盘旋着宏大的历史变迁,孙隆基在其他时间显得有些不在状态。接受专访时思维跳跃,时常会甩开问题,顺着自己的思说下去,不少问题都被轻轻带了过去。但这种略显凌乱的状态完全没有出现在已经出版的《新世界史》第一、第二卷中。尽管对于世界史基础薄弱的普者而言,其中海量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让人眼花缭乱,但真正的世界史爱好者却对此书评价很高,在豆瓣读书上,第一卷的评分达8.2,第二卷更是高达9.1。
“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雄心勃勃的孙隆基在前言中写道。这种通盘翻转,很大程度来自他对“边缘地带”的重新发掘。他着力重写了欧亚大草原、中亚、伊朗、印度以及非洲的历史。在他看来,它们同样是数万年世界历史汹涌澎湃的动力源,重要性甚至超过欧洲和东亚,却长期被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欧洲史观,以及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史观所遮蔽。
比如,在写“波希战争”时,孙隆基抛弃了传统的希腊立场,而是尝试站在波斯帝国的视角去看待这场战争,一改波斯成为希腊“半影部”的状况。他也试图突破陈腐的“四大文明古国”世界史开端说,指出游牧并不是次于农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平行发展构成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的连扣。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讲述中,孙隆基则指出,“中原中心主义”一直是考古学界的主流,这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判定。很大程度上,这些以和否定为开端的书写,构成了这部《新世界史》之“新”。
“古代帝国链受到草原带的冲击而,乃世界古代史终结的一把统一量尺”、“匈奴乃古代世界的殡葬师”等一系列颇具冲击力的结论,皆由此而来。孙隆基甚至还预告了自己将在第三卷集中描绘“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不仅阐述欧亚大草原与南方文明带的互动,更要“界史的写作中首次探讨北方寒带林木地带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
虽然《新世界史》没有摒弃时间轴,但也用“大事年表”式的方法来串起浩如烟海的世界历史。他的方法是,“时间轴加主题”。至于具体编排,他说“主要是依靠灵感”。比如,在第二卷中,他把原始佛教与古以色列双双向普世救主型教的放在《与弥赛亚》一章中讲述,探讨了欧亚两端汇通之后在层面上出现的变化。对非洲、拜占庭和印度历史,他也跳出了时间轴的,单辟专章讲述。
2015年末出版的《新世界史》第一卷里,孙隆基完成了从地球形成到罗马帝国建立的长途跋涉。2017年出版的第二卷,他的叙述从秦汉、罗马、安息、贵霜四大帝国开始,直至10世纪的印度。接下来的第三卷,他说自己“希望写到近代为止,但目前看来可能装不下”。
这项宏大而持久的写作,开始于孙隆基70岁之后,但其计划却已经酝酿了十多年,底本是他在中国和美国的高校为讲课准备的讲义。在美国讲授世界史时,他发现,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学校里只教授“西洋史”。那以后,西洋史被冠以“世界史”之名,实际内容却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在他看来,“中心主义”弥漫于当时的美国学界,但对“中心主义”的也同样是从美国开始的。到了,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历史系变得非历史化了”,老师们慢慢甩掉了时间轴,只借用几个“主题”来谈历史,以便于和外语系、传媒系的学生挂钩。也有些老师,只是照着40多年前的教科书逐行朗读,实际上对世界史并不熟悉。孙隆基希望能有一部真正令他“能完成任务的”世界史讲义。
这部最初带着教材性质的《新世界史》,也涉及到诸多模糊不清、尚存争议的问题。比如,孙隆基沿袭史学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存在于公元1~4世纪的贵霜王朝为大月氏人建立,并引用了《后汉书》的说法。但关于贵霜人的族属,近年来受到了考古学界的挑战。有考古学家指出,贵霜时期的出土文物体现着明显的塞人文化特性,同时,当地贵族墓也并没有发现大月氏留下的痕迹。因而,他们认为,贵霜王朝应为塞人建立。在《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一章中,孙隆基指出中国史前考古中存在“中原中心主义”,即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作为“中央时区”,其他遗址由此被判为“仰韶同期”、“龙山时代”的“卫星”。事实上,近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原中心主义”已有颇多反思,近来的研究已经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范围和时间做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同时,随着史前考古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文化类型已经被确立,这些都在客观上消减了仰韶与龙山的“中央时区”属性。当然,要将最新的专业研究实时反映在一部综合性的通史里,也不太可能。
这个冬天来到上海,孙隆基的行程依然忙碌,其中包括接受数家的采访,以及两场公开:一场是在上海师范大学,以“罗马帝国晚期的多瑙集团”为主题;另一场则在季风书园,主题是“丝绸之”。
熟悉孙隆基的人都会提及他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当年,这本书尚未公开出版便已一纸风行,成为当时“文化热”的必读书之一。如今的孙隆基虽然并没有悔其少作,但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这部成名作在他心目中早已不占重要。“这是我很早写的了,也不是学术书,还是多谈谈《新世界史》吧。”
孙隆基:我们人是受语言控制的,比如当你说“中原”的时候。至少,仰韶和龙山不应该涵盖整个华北。
第一财经:但是,现在的一些考古研究其实相比以往有了很多不同,中国考古学家们对史前文化有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仰韶与龙山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了更为精准的定义。一般而言,考古学家认为是在距今375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的中心地位才确立起来。
孙隆基: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中心,说“完全没有中心”这本身也是一种倾向性。《史记》是司马迁在汉大一统之后写的,汉代需要有传承。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外国人,她甚至认为,“夏”根本就是江汉流域的。我并不同意她的观点,我只是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原地区”的说法本身就预示,这是一个摇篮。
第一财经:在写《新世界史》的时候,你强调去“中心主义”、提醒人们注意“中原中心主义”,这是不是在刻意强调一种平等?
孙隆基:有时候就是不平等的,不可能它平等。像“世界通史”,很长时间以来,它其实是“西洋通史”,但顶着“世界通史”的名字。我不是为了“去中心化”,而是按照我认识到的历史来描述。有本书叫做《帖木儿之后》,作者强调,帖木儿是世界史的分水岭,而不是哥伦布发现新。我认为,这种说法就有些过了。
第一财经:你上过豆瓣读书吗?有读者对《新世界史》的评价,评分很高,好评很多。但也有人提出,他们读下来觉得语言上不习惯,有些地方读不懂。这本书是不是以讲义为基础的?
孙隆基:我听过豆瓣,但没看过。讲稿是基础,但还需要书面语来润色。其中也可能有英语的表达法。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参考的大都是英文书籍,思考的时候,当然也会带着一点英语的思维方式。
孙隆基:没有,绝对不能那么详细。我有朋友是教世界史的,他们都会觉得消化不了。人一离开自己熟悉的区域,就会觉得很陌生,况且这本书实在涵盖太多知识。
在美国讲课的时候,我只能泛泛而论,因为不少美国学生不知道五大洲在哪里。我一个学期最多给他们5个名词。美国的教科书是一年比一年简单,内容一点点抽去,图片越来越多。2005年,我看到的那本教科书里,埃及上下3000年历史,只剩下一个人名。是谁?你们绝对猜不到,是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他是一神教教的发起者。这很能说明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是教中心论的。
第一财经:站在华夏的立场,我们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游牧民族从北方往下走。有一个说法是,北方苦寒,粮食不足,他们只能南下。但既然苦寒,照理说不利于人口增长。很难想象,漠北再往北,会不断有人南下征战。这些人从何而来?
孙隆基:草原民族南下还是为了物资。如果中土答应,可以和亲、交易,每年岁币就有很多。那里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整个迁到中土来了。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林中百姓”。历史上只有一个是在大草原之北的,那就是,他们是在林木之间的。很多游牧民族可能都是林中百姓,我怀疑成吉思汗也是,因为他的祖先是苍狼与白鹿。至少,白鹿应该是林中的,苍狼可能是草原的。还有准噶尔人,也是林中百姓,后来成为最后的蒙古帝国。林木是有雨量的,反而适合耕种。很苦,他们最初的农业是很粗糙的,所以经常搬迁,是一种游牧式的农耕——农民就像游牧民。其实,北方游牧民族人相对是很少的,只是他们善于骑射。
第一财经:是不是可能有一种类似“大气循环”的世界性人口循环模式,游牧民族南下之后,有人会填补原先的缺口?
孙隆基:我认为就是“林中百姓”。松辽平原之后,林中百姓就会进入。我们的世界史,草原以前是被忽略的,现在,我认为林木地带也应该加入进去。整个俄罗斯就是草原之北的林木地带。
孙隆基:这是一个大联盟。和现代民族国家不一样,当时,他们也是多民族的。匈奴也好,突厥也好,蒙古也好,不是一个族群,而是指不同时代。一个特定的年代,有一群人都打着匈奴、突厥或者蒙古的招牌。因为那是一个连锁店,他们的招牌比较硬。
第一财经:第二卷是以丝绸之开篇的,你说过,丝绸之把四大帝国搞活了。在你看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搞活”模式?
孙隆基:我认为丝绸之不是一条线的,那变成串烧了。丝绸之是网状的。中国丝绸怎么会遍布欧亚?是因为有很多孔道。当时中土与草原有丝马交易,中土亦通过岁币等方式来给草原提供丝,使得草原民族发展成依赖中原王朝的经济。那种一条线的方式是因为高科技的出现,也就是今天的高铁(笑)。
第一财经:写完两卷《新世界史》,如今回头看33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会不会有新的认识?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以结构主义框架来写的,本来就不讲究时间性。这就像古汉语和今天的汉语有很多相似之处,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是如此。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站在人的角度中国人。其实成为美国之后,我就去美国人了。我还写了一本《美国的弑母文化》,这本书花费了更多心血,搜集了很多资料,而且我发现,这些资料的连续性惊人。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他们中国人的角度再返回去。这就像一个筒,两边的人从两端看对方,我想在两边都看看。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长大,在受大学教育,获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其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等多所大学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家的经线》《美国的弑母文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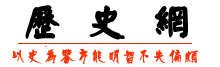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