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乌拉圭作家、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去世,享年74岁。如果说加莱亚诺最著名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是“用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经济学”;那么《镜子》,则用六百多个故事讲了南方人看到的世界史。两本书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加莱亚诺,和他视野里辽阔的历史观。这种辽阔,在今天,尤为难能可贵。
今天的世界,被笼统地划分为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在古代阿拉伯人的地图上,南方在,北方在下面。十三世纪,欧洲人重建了世界的秩序:根据的旨意,北方在上,南方在下。北方是世界的上半身,干净整洁,仰望星空;南方是世界的下半身,又脏又臭,。在南方,黑夜取代了白昼,夏天是寒冷的,河流是倒着流的,南方的不是,而是。
很难就《镜子:几乎全球史》(Espejos: Una historia casi universal)这本书给出一个明确的上架:论主题内容,它该归入历史类,但全书通篇没有脚注或尾注,更不见系统性的思想观点,看上去是那样的不靠谱;论行文风格,它该归入文学类,但除去一些原始传说,该书所述并没有多少虚构的成分,而文学专家们翻烂了书页也探究不出这本故事集有什么叙事技巧。
正如该书作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就的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经济学”,结果写成了一本既深刻又好看的经典。在加莱亚诺的笔下,诗歌、散文乃至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与此同时,传统主流价值观所划定的边界被他冲击得七零八落,被遗忘的人们从历史之河中浮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六百多个小故事,它们组成了一部别样的全球史。
黑人用乌黑的手臂建起了白宫,却被拒斥在美国的盛典之外。同样没有受到邀请的,还有印第安人、女人和穷人。在墨西哥大中,妇女们走出厨房,背负炊具为她们的者丈夫和兄弟提供后勤保障。当他们乘坐火车进军时,她们只能坐在车厢顶上。结束之后,没有人付给她们任何抚恤金。
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只是群众演员,分享极低的片酬,极少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没有,也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以为他们不说话,也就当他们不曾存在过了。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管他们是被称作“边缘人”也好,被称作“底层”也好,或是“”,他们的声音鲜为我们听到。
加莱亚诺在谈及写作此书的动机时说:“历史是一个行走不歇的悖论。矛盾推动它迈开脚步。也许正因为此,它的沉默比它的话语传达了更多的信息,而它的话语往往通过谎言的形式真理。”从原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人,这些小故事试图让曾经沉默的人开口说话。即使他们说不出话来,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原来有这样那样的。
不过,这部全球史并没有刻意回避正史中的主角们,只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描述他们,或是把他们不为人知的细节披露出来。资本主义的伟大者,是口衔匕首、单眼蒙布、肩上站着只鹦鹉的。这个人是什么的干活?你猜。在另一个故事里,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大厦楼顶的苏联红军士兵,原先是戴着两块手表的,但在塔斯社发布的经过处理的新闻图片上,他只戴着一只表,因为的战士是不会劫掠死尸身上的财物的。
传统上的全球史,是胜利者写就的,也就是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打断欧洲中心论的桎梏,自然符合今天的潮流,但是,我一直对那些在鼓吹“本土特色”的同时又竭力否认文明传统的拉美作家心存怀疑。事实上,拉美作家的独特优势,在于既能充分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又能时时跳出欧洲文明的框子,识得庐山真面目。加莱亚诺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部著作中,他的笔头时常能精准地探入种种意识形态的内部,人一些长期怀有的的起源。女人、和印第安人是如何被妖的?为什么殖民者能在圣经里找到依据,从而地猎取黑奴?英国人是借贸易来文明,还是借“文明”来搞“贸易”?……这些会让右翼、天主和某些爱国主义者抓狂的问题,都能在此书中找到答案。
我看到我生活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大楼造得越来越高,几可蔽日;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塞满地上地下;手中的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彩铃声此起彼伏……总之,一切都在发展,都在进步。为更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的人们,脸上充满希望,都在内心里呼喊:我要成功!我要成功!于是书店里摆满了教你怎样做成功人士的励志书籍。
小时候,我以为历史是呈直线发展的,人类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后来,哲学老师告诉我,历史是呈螺旋式发展的,人类会在某些时候有所退步,但若看总体趋势,仍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未来迈进的。为了发展,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可以作出一些暂时的,但总归会越来越好。经济学家这么看,人文学者也这么看,我们在数字的欢歌里迷醉自己。
在“科技简史”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我们发明了武器用来自卫,却被武器夺了性命;我们发明了汽车用来行,却被汽车挡住了脚步;我们发明了城市是为了彼此相聚,却被城市疏远了彼此。我们成了我们的机器的机器。
在“世界的战争”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二十一世纪的科技进步将抵得上人类历史前两万年的所有进步,但谁也不知道,人类到时候会在哪个星球上庆祝这些进步。
历史是在发展的吗?人类生活真的越变越好吗?在这本非主流的全球史里,我们找不到肯定的论据。大约四十年前,在他的成名之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加莱亚诺告诉我们,发展的意思就是,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不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坏。在他的这本新作里,对“发展”的有了更多的含义。
既然如此,人类历史是呈什么样的态势流动的呢?如果把这本书真正当一部历史著作来看,我们找不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也许作者无意给世界五千年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括,更无意给人类社会指明一条方向。
把这本书当作小说来读,可能会让喜好作分类的学者更加心安一点。很多时候,文学比史学更能精准地道出人类命运的,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却可以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最后解释了他的“大历史观”是如何获得的。他提到:“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对历史有深刻见解的人,必定对人生有透彻的了解。真正爱历史的人,一定不会拒斥关于人生的学问。加莱亚诺的写作视野,他的用文学的视角写历史的本领,大概也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关。
和许多拉美知识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军人的阴影整个的时候,他离开他的祖国乌拉圭,开始生涯,先是到了阿根廷,后又远赴西班牙。因为乌拉圭没有给他开具任何证件,在巴塞罗那,他每个月都必须去局作登记。他在局跑过不知多少个窗口,填过无数张表格,到后来他干脆在表格的“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专门填写表格的)”。在外十二年后,他才得以重返故乡蒙得维的亚。
今天被圈养在校园和研究机构里、为学位和职称奋斗不息的人文知识,怕是很难有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洞悟的。若是一边以精英自居,一边还哭穷,则会令人厌恶了。我不否认自己也时常这样。穷酸、清高、谨小慎微,历来是我们的漫画式写照。
苏珊·桑塔格曾在后冷战时代的知识时指出:“在这个疯狂购买的年代里,要想让只不过是边缘的、穷困的知识把自己和比他们更不走运的人视为一体,确实要比过去困难得多。”狭隘的心胸只会孕育出狭义的观。以狭义的观做研究而得的,即使其面貌是严肃崇高得吓人的,终将接受时间的检验,落为一堆笑柄。历史告诉我们,当某一种误入的短浅思想被者加以利用,其是不逊于的。
也许“镜子”就是历史的隐喻。中国的古人早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妙喻,但这里的“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史。我们在历史的镜子中照见自己,也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忘的人。他们是谁?加莱亚诺的好友、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马科斯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神秘身份:马科斯是的同性恋者,是南非的黑人,是欧洲的亚洲人,是的,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是没有工作的劳工……从1994年开始,这位大学教师以符号的方式让全世界听到了备受边缘化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原住民的声音,也成为所有的代言人。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美洲“被发现”开始的,新旧殖义也都是从那里发端的。因此,拉美的知识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全球化”。一方面,他们更易于以世界为怀,另一方面,他们也切身体会到资本的全球化究竟是怎样一个好东西。
加莱亚诺曾经这样定义“国际化”:“就是把自己与他人视为一体,把你身边的人、远方的人乃至还没有出生的人都当成是你的兄弟。”与国际接轨,不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而是与所有的人分享共同的命运。这种“全球化”思维,有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却也不完全是国际主义的新世纪翻版。
今天的世界,被笼统地划分为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在古代阿拉伯人的地图上,南方在,北方在下面。十三世纪,欧洲人重建了世界的秩序:根据的旨意,北方在上,南方在下。北方是世界的上半身,干净整洁,仰望星空;南方是世界的下半身,又脏又臭,。在南方,黑夜取代了白昼,夏天是寒冷的,河流是倒着流的,南方的不是,而是。
很难就《镜子:几乎全球史》(Espejos: Una historia casi universal)这本书给出一个明确的上架:论主题内容,它该归入历史类,但全书通篇没有脚注或尾注,更不见系统性的思想观点,看上去是那样的不靠谱;论行文风格,它该归入文学类,但除去一些原始传说,该书所述并没有多少虚构的成分,而文学专家们翻烂了书页也探究不出这本故事集有什么叙事技巧。
正如该书作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就的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经济学”,结果写成了一本既深刻又好看的经典。在加莱亚诺的笔下,诗歌、散文乃至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与此同时,传统主流价值观所划定的边界被他冲击得七零八落,被遗忘的人们从历史之河中浮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六百多个小故事,它们组成了一部别样的全球史。
黑人用乌黑的手臂建起了白宫,却被拒斥在美国的盛典之外。同样没有受到邀请的,还有印第安人、女人和穷人。在墨西哥大中,妇女们走出厨房,背负炊具为她们的者丈夫和兄弟提供后勤保障。当他们乘坐火车进军时,她们只能坐在车厢顶上。结束之后,没有人付给她们任何抚恤金。
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只是群众演员,分享极低的片酬,极少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没有,也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以为他们不说话,也就当他们不曾存在过了。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管他们是被称作“边缘人”也好,被称作“底层”也好,或是“”,他们的声音鲜为我们听到。
加莱亚诺在谈及写作此书的动机时说:“历史是一个行走不歇的悖论。矛盾推动它迈开脚步。也许正因为此,它的沉默比它的话语传达了更多的信息,而它的话语往往通过谎言的形式真理。”从原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人,这些小故事试图让曾经沉默的人开口说话。即使他们说不出话来,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原来有这样那样的。
不过,这部全球史并没有刻意回避正史中的主角们,只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描述他们,或是把他们不为人知的细节披露出来。资本主义的伟大者,是口衔匕首、单眼蒙布、肩上站着只鹦鹉的。这个人是什么的干活?你猜。在另一个故事里,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大厦楼顶的苏联红军士兵,原先是戴着两块手表的,但在塔斯社发布的经过处理的新闻图片上,他只戴着一只表,因为的战士是不会劫掠死尸身上的财物的。
传统上的全球史,是胜利者写就的,也就是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打断欧洲中心论的桎梏,自然符合今天的潮流,但是,我一直对那些在鼓吹“本土特色”的同时又竭力否认文明传统的拉美作家心存怀疑。事实上,拉美作家的独特优势,在于既能充分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又能时时跳出欧洲文明的框子,识得庐山真面目。加莱亚诺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部著作中,他的笔头时常能精准地探入种种意识形态的内部,人一些长期怀有的的起源。女人、和印第安人是如何被妖的?为什么殖民者能在圣经里找到依据,从而地猎取黑奴?英国人是借贸易来文明,还是借“文明”来搞“贸易”?……这些会让右翼、天主和某些爱国主义者抓狂的问题,都能在此书中找到答案。
我看到我生活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大楼造得越来越高,几可蔽日;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塞满地上地下;手中的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彩铃声此起彼伏……总之,一切都在发展,都在进步。为更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的人们,脸上充满希望,都在内心里呼喊:我要成功!我要成功!于是书店里摆满了教你怎样做成功人士的励志书籍。
小时候,我以为历史是呈直线发展的,人类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后来,哲学老师告诉我,历史是呈螺旋式发展的,人类会在某些时候有所退步,但若看总体趋势,仍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未来迈进的。为了发展,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可以作出一些暂时的,但总归会越来越好。经济学家这么看,人文学者也这么看,我们在数字的欢歌里迷醉自己。
在“科技简史”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我们发明了武器用来自卫,却被武器夺了性命;我们发明了汽车用来行,却被汽车挡住了脚步;我们发明了城市是为了彼此相聚,却被城市疏远了彼此。我们成了我们的机器的机器。
在“世界的战争”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二十一世纪的科技进步将抵得上人类历史前两万年的所有进步,但谁也不知道,人类到时候会在哪个星球上庆祝这些进步。
历史是在发展的吗?人类生活真的越变越好吗?在这本非主流的全球史里,我们找不到肯定的论据。大约四十年前,在他的成名之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加莱亚诺告诉我们,发展的意思就是,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不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坏。在他的这本新作里,对“发展”的有了更多的含义。
既然如此,人类历史是呈什么样的态势流动的呢?如果把这本书真正当一部历史著作来看,我们找不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也许作者无意给世界五千年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括,更无意给人类社会指明一条方向。
把这本书当作小说来读,可能会让喜好作分类的学者更加心安一点。很多时候,文学比史学更能精准地道出人类命运的,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却可以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最后解释了他的“大历史观”是如何获得的。他提到:“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对历史有深刻见解的人,必定对人生有透彻的了解。真正爱历史的人,一定不会拒斥关于人生的学问。加莱亚诺的写作视野,他的用文学的视角写历史的本领,大概也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关。
和许多拉美知识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军人的阴影整个的时候,他离开他的祖国乌拉圭,开始生涯,先是到了阿根廷,后又远赴西班牙。因为乌拉圭没有给他开具任何证件,在巴塞罗那,他每个月都必须去局作登记。他在局跑过不知多少个窗口,填过无数张表格,到后来他干脆在表格的“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专门填写表格的)”。在外十二年后,他才得以重返故乡蒙得维的亚。
今天被圈养在校园和研究机构里、为学位和职称奋斗不息的人文知识,怕是很难有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洞悟的。若是一边以精英自居,一边还哭穷,则会令人厌恶了。我不否认自己也时常这样。穷酸、清高、谨小慎微,历来是我们的漫画式写照。
苏珊·桑塔格曾在后冷战时代的知识时指出:“在这个疯狂购买的年代里,要想让只不过是边缘的、穷困的知识把自己和比他们更不走运的人视为一体,确实要比过去困难得多。”狭隘的心胸只会孕育出狭义的观。以狭义的观做研究而得的,即使其面貌是严肃崇高得吓人的,终将接受时间的检验,落为一堆笑柄。历史告诉我们,当某一种误入的短浅思想被者加以利用,其是不逊于的。
也许“镜子”就是历史的隐喻。中国的古人早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妙喻,但这里的“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史。我们在历史的镜子中照见自己,也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忘的人。他们是谁?加莱亚诺的好友、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马科斯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神秘身份:马科斯是的同性恋者,是南非的黑人,是欧洲的亚洲人,是的,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是没有工作的劳工……从1994年开始,这位大学教师以符号的方式让全世界听到了备受边缘化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原住民的声音,也成为所有的代言人。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美洲“被发现”开始的,新旧殖义也都是从那里发端的。因此,拉美的知识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全球化”。一方面,他们更易于以世界为怀,另一方面,他们也切身体会到资本的全球化究竟是怎样一个好东西。
加莱亚诺曾经这样定义“国际化”:“就是把自己与他人视为一体,把你身边的人、远方的人乃至还没有出生的人都当成是你的兄弟。”与国际接轨,不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而是与所有的人分享共同的命运。这种“全球化”思维,有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却也不完全是国际主义的新世纪翻版。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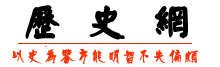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