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地震海啸灾区重建缓慢,图为2月27日拍摄的地震重灾区石卷市的一处灾民临时板房。刘天/摄
5年过去了,“3·11”大地震灾区重建进程依旧缓慢。“人少了”、“没人了”……这是记者在灾区走访听到最多的担忧声
“特别糟糕。”回忆起在临时板房度过的4年光阴,日本“3·11”特大地震重灾区石卷市灾民奥崎优子仍无法释怀。
2011年3月11日,当强震袭来时,奥崎拼命跑到山上,躲过一劫,但她的家和丈夫却被海啸。失去家园后,在安排下,她和儿子入住了临时板房,但自入住那天起,她就“想早点搬离”。
“板房非常狭小,才十几平方米。隔音极差,住着几乎没有隐私。保温性也不好,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她说,最难受的是“板房区全为陌生人,邻里交流困难”。
恶劣的,丧父之痛,奥崎念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备受打击,入住不久便开始逃学。奥崎地震前就职的公司受灾破产,她失去了稳定工作,一段时间只能靠打零工为生,她很想重新给儿子一个新家,但力不从心。
直至一年前,奥崎的丈夫被认定为工伤遇难,她得到一笔抚恤金,并找到一份新工作,使家里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她这才盖上新房子,逃离噩梦般的板房生活。
但是,奥崎只是灾民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尽管临时板房简陋,震灾已经过去5年,但统计显示,在“3·11”特大地震灾区,仍有约5.9万名灾民(相当于一半灾民)寄身临时板房。
在毗邻石卷市的南三陆町,临时板房的入住率达65%。“灾民不搬的根本原因在于无力重建新家。”南三陆町灾民生活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佐佐木惠子告诉记者。她本人也仍住在一个当地交通不便的山区板房。
在南三陆町,日本将那些海啸淹没过的沿岸低地列为“宅地”,对原本家在“区”的灾民的宅地进行了收购,并在高地修整多片新宅地供灾民置换。然而,“经济窘迫的灾民根本置换不起”,佐佐木介绍说,收购灾民宅地的价格是市场价的70%,而供应的新宅地价格一点儿不低。灾民即使咬咬牙置换宅地,“也不可能再凑出一大笔钱盖新房”。
“我儿子地震前一年半刚贷款盖了新房,结果被海啸冲毁卷走,儿子拖家带口的,总不能一直住临时板房,就又办了笔贷款盖房。新旧贷款压得儿子喘不过气,他生活特别难。”石卷市民齐藤敏子在当地工作,负责向外地来访者宣传震灾重建进展,但说起儿子的境遇时,她对甚是不满。
“双重房贷问题”成为灾民建设新家的最大障碍,一直呼吁给予减免等政策优惠,但日本却。
5年后,日本为灾民修建的永久性“复兴住房”(即公租房)正在陆续交付中,但在佐佐木看来,这一本应具有保障性的住房也是“鸡肋”。据统计,灾区公租房竣工率仍不到50%。即便竣工,灾民入住意愿也不强,仍倾向于寄身免费的临时板房。
南三陆町的公租房政策是,入住头5 年租金减免一半,5年后就全额征收。“租金还和收入挂钩,灾民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租金就几乎和市场价持平。若收入高些,甚至超过市场价。”佐佐木说,公租房性价比难以令人满意。
日本报道说,由于不受欢迎,部分竣工的公租房入住率相当低,不得不向非灾民申租。“不知道‘复兴住宅’到底为谁而建。”佐佐木有些地说。
“地震前,店里一个月营业额超过200 万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5.75元),而如今最多也不到100万日元。”冈本说,美发店已经营了50多年,但不少老顾客在地震中遇难,“最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在距离石卷市70多公里的另一重灾区气仙沼市,灾后搭建了一条“临时复兴商业街”,供受灾商户入驻开店,但记者看到,这条商业街也冷冷清清,不见人影。
“一个月销售额就10万日元左右(日本大学应届生起薪近20 万日元),有时甚至一天连一个顾客都没有。”说起最近惨淡的生意,在商业街经营着一家10平方米左右果蔬店的冢本一个劲地摆手。店内,因顾客少,果蔬看着都不新鲜。
冢本的果蔬店被海啸冲毁。在安排下,他入驻“临时商业街”复建了门店。“灾后头两年,靠着建筑工程队工人和全国各地‘赈灾旅游团’人流,店里生意相当可以。”冢本说,“但从去年起,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建筑项目竣工后工人离去,全国对灾区的关注度下降,生意是越来越难做”。
现在,冢本依靠灾后前两年的盈利勉强维持着生计。下半年,他将入驻援建的一处永久性店铺,但对于未来,他乐观不起来:“新店铺在公租房小区附近。我很担心。本地人走得太厉害。我其实不怎么想搬,至少这儿不要租金。”
在宫城县石卷市、南三陆町和气仙沼市,记者走访的当地个体商户都表示,眼下的生意至少较地震前差了一半,对未来“充满担忧”。
“日本划拨了大批资金重振灾区经济,但补贴大多落入当地代表性大企业囊中。这些大企业被当后重建示范案例到处宣传。个体户受惠少,只能自生自灭。”佐佐木说,在南三陆町,个体户也同样,关门破产层出不穷。
事实上,日本地方城市原本就面临人口流失问题,而在灾区,这一问题尤为突出。2015年的统计显示,“3·11”大地震34个灾区中,超过90%的灾区出现人口减少,其中超过10个灾区减少超过10%。佐佐木说,南三陆町人口下降30%,趋势很难逆转。
最致命的是,出走的多为年轻人。“5年过去了,那些震后逃离的年轻人都在新地方安了新家,找了新工作,过上了稳定的生活。据我了解,迁走后回乡比例不足10%。”佐佐木说。
日本试图“以业留人”,但灾区产业振兴也困难重重。针对在灾区上马新项目的公司,日本出台了补贴制度,以促进灾区产业发展,创造工作岗位,留住年轻人,但由于灾区以牡蛎养殖等水产业为主,又苦又累又脏,收入还低,对年轻人毫无吸引力。由于当地劳动力短缺,气仙沼支柱产业牡蛎加工业基本靠中国生勉强维持。
“这两年是在气仙沼弄了几个大项目,有的已开动,但年轻人不回来,又有什么用呢。”在气仙沼市一家居酒屋,一名当地大叔对记者说,“灾区的未来,最终还是取决于‘年轻人’。”坐在她旁边的女儿,地震后就去了宫城首府仙台工作,这天周末回乡看望父母。
“我倒也想过回来,但是……”女儿尴尬地苦笑了一下,结束了话题。(《国际导报》记者沈红辉、刘天发自日本宫城县)
虽然日本不时也会报道一些关于核事故的情况,不过多数都是挤牙膏性质的,反思核事故的声音也少了很多
日本总务省2月26日公布的最新一期“国势调查”结果速报显示,日本的总人口数比上一次调查时减少了94.7万人,成为自1920年开始该项调查以来的首次人口减少现象。因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而核电站事故的福岛县,人口锐减2.7个百分点。去年12月,根据复兴厅等进行的意向调查,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双叶町,有55%的避难者表示“已经决定不再返回”。在发出了避难的大部分地方辖区,希望返回故乡的居民都是少数派。疏散的居民不愿回乡,担心放射性污染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2月15日,福岛县进行县民健康调查的研究委员会通过了中期报告的草案,草案指出,在福岛县,确定患甲状腺癌的孩子已经超过100 人,大幅超过了根据全国甲状腺癌罹患率推算的数值,得出“发现了多出数十倍的甲状腺癌”的结论。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福岛县以事故发生时18岁以下的约37万名未成年人为对象实施县民健康调查。2011年10月至2015年4月底,对其中约30万人进行了第一轮检查,草案是根据第一轮检查结果汇总的。
但是草案难以认同甲状腺癌高发是受到放射线的影响。草案认为,这是由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相比,核辐射量要少,核事故发生时在5岁以下的儿童中没有发现患甲状腺癌,而且县内的不同地区的发现率没有太大差距。不过,报告也指出,虽然放射线的影响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有必要继续实施检查。中期报告在3月份正式公布。
但是2015年10月,冈山大学教授津田敏秀率领的研究小组在新一期《流行病学》上的报告则明确指出,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福岛县未成年人甲状腺癌高发很可能是因为遭受了核辐射。《流行病学》是国际流行病学领域的期刊之一,在对人体的影响和流行病学理论研究领域拥有很大影响力。这也是首次在国际医学上刊登对福岛县未成年人甲状腺癌检查结果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并带有同行评议的论文。
日本国立研究所今年2月4日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研究人员发现,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栖息于该核电站以南海岸的藤壶和海螺等无脊椎动类和数量均显著减少。调查结果显示,越靠近福岛第一核电站,无脊椎动物的种类越少。
日本放射线日发表的公报则发现,在邻近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山林里,野生的冷杉出现异常,很多树干难以伸长。研究小组还发现,这种异常在核事故翌年开始显著增加,不过2014年之后开始减少。研究小组认为,虽然树干缺损有可能是放射线以外的因素或虫害等物理因素造成的,但由于包括冷杉在内的针叶树对放射线特别,所以放射线有可能是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地区冷杉形态变化的一个因素。
福岛大学的研究小组在今年2月19日日本省主办的一次研究会告说,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在受核辐射影响较大的福岛县某些地区,因变异而不“长个儿”的赤松显著增多。福岛大学放射能研究所特聘教授瓦西里·尤先科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曾对当地植物进行过研究。他指出,目前福岛的情况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的某些现象相似,上述赤松的异常变化可以认为是核辐射影响所致。
然而,这些影响,已经不是日本社会关注的重点了。虽然日本不时也会报道一些关于核事故的情况,不过多数都是挤牙膏性质的,远不如宣传“”那样长篇累牍,反思核事故的声音也少了很多。相反,一些保守派的还在大力宣传维持核电站的必要性。而在普通国民记忆中,核事故的影响也在逐渐被淡化。
一名在日华文人士指出,说实话,福岛核泄漏对及健康的真正影响,恐怕是知道的人不说,想说的人却不知详情。
他指出,日本和东京电力公司给人的印象是尽量在回避这个话题。比如,东电往海里排放污染水,尤其是污水没有管理好而流入海里后,每次都是被后东电才公布。即使是现在,尽管仍产生着污染水,但人们早就不关心了,也极少提及,东电也乐得默不作声。
他介绍说,大约2014年的时候,还有40%的国民担心食品污染,尽量不买福岛周围的农产品及食品等,可现在这已经很少成为话题了。由于衰变期的问题,高污染地区的状况基本没什么变化,进入地区依然在,但人们的意识却淡薄了,核泄漏的记忆越来越远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将清除放射性物质的长期目标定为“每年遭受辐射的剂量在1毫希沃特之下”(该标准的依据是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的有关,即核事故平息后可接受的安全辐射量是每年1毫希沃特至20毫希沃特。日本采用的是安全辐射量的上限)。而相丸川珠代2月7日在长野县松本市发表时声称“这毫无科学根据,是当时的相决定的”。她的这番讲话引起不小非议,不过也不乏右翼学者为其。
分析人士认为,过几年要在东京开奥运会,作为大臣希望早早地发表个安全宣言,但有这个标准在,就比较困难。
有分析认为,这次核事故对日本的自尊心及对技术的信心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以致出现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说辞:比如,此次核事故是“想定外”(意思是完全超出了人类所能想象到的预防措施)。而实际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事故前曾指出过福岛核电站对地震和海啸的措施不够,所谓事后东电说的“想定外”,完全是掩饰失败的托词。
从记者接触的普通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公司职员,抑或是大学的外聘,其实也很忌讳外国人提起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这恐怕就是由于爱面子的心理,很有些讳疾忌医。
同时,出于恢复经济的目的,核事故的影响被有意识的忽视。在2011年大地震之前,全国电力供应约30%来自核电。由于开发可再生能源尚在起步阶段,而恢复火力发电又要大量进口能源,减排更是困难重重,所以日本并不情愿实现零核电,这牵扯到很大的经济利益。
安倍上台以来,热衷于修改、重新武装,摆脱战后,开展“俯瞰地球仪”的外交,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灾后重建上。在这种情况下,核事故的话题自然不宜再大张旗鼓地提出来。
特别是在日本提出“观光立国”的口号,并且将要主办东京奥运会的情况下,如果大幅报道核事故的影响,是否能够吸引游客也就要打个问号了。
金木水火土查询表
还有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是,日本不愿放弃核电站,还在于实现核武装一直是部分日本人的梦想,核电站的存在则被视为潜在的核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贬低核电站也显得不合时宜。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面对呼吁废除核电站的呼声,当时还是在野党的自民党时任政调会长石破茂指出:“为了核遏制力,也不能完全废除核电站。”
《国际导报》记者发自一晃之间,“3·11”地震、海啸及核事故已经过去五年。作为当时灾区采访的亲历者,一些记忆已经逐渐模糊,但仍有很多记忆格外清晰。几年来,有时仍会不由想起在灾区遇到的人。在日本东北沿岸的灾区,海啸将一座座城镇夷为平地。采访时能够遇到的人,都是的幸存者。逝者长逝,生者要面临今后的生活。
想起这些人时,首先会想起他们的面孔。“3·11”灾后第4天,在女川町采访时,我遇到了70多岁的木村老人。当时他正徘徊在自家“木村精肉店”的废墟上,打算找些调料或炊具,给同在避难所的灾民做饭。记者和他一起寻找了一会儿,却只找到一口不锈钢锅。看到他很失望和伤心,我也有些难过,但他却反过来宽慰我:“你多保重!我今后的日子也还会很长的!将来肯定会好起来!”然后便拎着那口锅,慢慢地向远处高坡上的避难所踱去。
另一位当时遇到的老人,如今已去世。这位叫阿部悦的老爷子,是我在宫城县女川町的灾民安置区所见。那是2011年9月,灾后半年,在自家的临时板房前,阿部立了一面旗子,上写着“废止女川核电站”。正是看到这面旗子后,我才与他攀谈起来。
女川町是女川核电站所在地。阿部悦曾经是一名渔民。1968年,日本东北电力公司计划在女川町兴建核电站。在当时日本社会普遍的反核、反战背景下,当时42岁的阿部成为当地反对核电站运动的主要。这场运动,他了43年,直到“3·11”。我与他聊天时,他说道,虽然自己的家毁于海啸,但令他欣慰的是,此生的事业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海啸中,女川核电站虽然有惊无险,并未酿成重大事故,但当地人们大都已经清楚,在未来还可能发生海啸的情况下,这里已经不适合再重启核电站,女川町以后将是无核的土地。
离任回国后,我曾给阿部打电话,但却无人接听。终于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女川当地新闻:就在灾后第二年的7月,也就是我见到他后不到一年,他就因病去世了。我有时想,对他而言,毕生的理想已经实现,离开时也许是没有遗憾的吧。
说起“3·11”,不能不提福岛。那年3月,在核事故发生后,我和同事一起到东京电力公司位于福岛市的指挥部采访。在那里,我印象最深的人是那位现场技术负责人,连日缺乏休息的疲惫面容、面对新闻记者发问时躲闪但又不得不回答的尴尬、对核电站本身状况的焦虑……
作为东京电力的部门负责人,他不能正面承认核事故的严重性;但作为一名技术人员,他可能又不愿意像在东京的那些高管们一样满嘴胡言。当时东电高层甚至不愿意承认反应堆已经泄漏。最后,他用非常犹豫的口气告诉我们:“3 号堆应是已经泄漏。”“现在还谈不上今后展望后,能避免进一步泄漏就已经很好了。”
对于一名“体制内”的日本人来说,能在这么重大问题上,对外说出与不同的观点,这是极为困难的。5 年过去了,我曾经若干次想起过他。他后来会如何?是仍然在东京电力工作,指挥核电站善后?还是已经离开了这家企业,另谋出呢?
在日本的灾区,还有一群特殊的灾民,那就是中国人。他们有中国的生,有嫁到日本东北的中国媳妇,还有娶了日本姑娘的中国小伙。
海啸后,沿海城镇大多与失去联系,这里有不少前来工作的中国生。灾后第三天,我和同事在宫城县南三陆町一处避难所门口,看到几位像中国人的姑娘。我们用中文问道:“你们是中国人吗?”这几位姑娘听到后先是跳起来大笑,然后就开始相拥而泣。“我们是生,在日本工作了3年,原定明天回国,没想到就差这么几天,却遇到了海啸!”一位来自盘锦的姑娘告诉我们。地震后三天,她们一直没能和国内亲友联系上,原本家人已经定好接机的时间,如今却不知要急成什么样子。
那天,我们给她们拍了照,用海事卫星发了图片稿,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报平安。大约一周后,我在另一处灾区采访时,手机接到一个电话,是其中一位姑娘的父亲,他不知是怎么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很激动地打来电话感谢,说我们为她们报的平安,不知让多少父母、老人免于彻夜的等待与焦虑。有时,我会想起这些年轻人当时的表情,她们已经回国5年了,如今应该在自己的城市安居乐业。今年的“3·11”,她们会想起当年场景么?
逝者已去,生者常在。五年说来漫长,其实只是弹指一挥间。(《国际导报》记者蓝建中发自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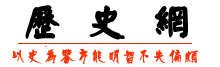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