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学人就如何进一步把中国学术推向世界,并在国际学术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近些年来,中国学人就如何进一步把中国学术推向世界,并在国际学术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展开度、多层次、多学科的深入探讨。有关“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讨论,除了要有持续性、要从理论上发掘新的见解,从具体的学术工作中发现新的,还要有耐心,以求铢积寸累之效。
习总“5·17”重要讲话从新时期国家战略高度,论述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及承担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幅高起点的、前瞻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这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按照自身发展特点,精心描绘出在这幅宏伟蓝图中的所在。
对于一件重要事情的重要性认识,有没有自觉性决定了认识的高度。这种自觉性来源于时代的启迪和历史的。“5·17”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界前列。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读了这段话后,联系中国“走界前列”,后来受到列强侵略,又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了伟大民族复兴道的曲折历史,能够深刻体会到“5·17”重要讲话激发人们自觉的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感的自觉认识,既来源于现实,又来源于历史,它表现为豪迈的有作为、敢担当的奋发。
有了自觉性,还要有自信心。近百余年的学术史表明,当中国近代学术起步之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已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因此,“引进”为我所用是现实的选择。一方面来看,中国学人了解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学人放松了表现“”。对于中国文化优秀遗产尤其是优秀的学术遗产缺乏集中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人的学术和理论自信心。面对中华优秀文化这座思想、理论、学术的富矿,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理应具有充分的信心。
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从何处入手?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5·17”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投入等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总进而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包含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在这三个特点中,继承性、民族性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脱离了继承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性,没有民族性,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首先从继承性、民族性入手。
谈到话语体系,必然涉及有关理论问题,包括概念、范畴等学术用语。从中国古代史学来看,记述历史的著作浩如烟海,而讨论理论问题的专书却并不多见,人们关于历史的认识和关于史学的认识,多散见于各种著作之中。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后人对理论问题发掘、梳理,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记述、没有理论。可以说,这种情况不止是史学如此,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情况。以史学研究为例,可从两方面来加以关注:其一,不应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方著作来反衬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一则是时代不同,二则是中人在理论思维与表述上的特点不同,作简单的比较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表达散于各书,以至于显示不出其理论魅力,但却因中华文明不曾中断而使不同时期的学人可以以“接力”的方式,传承着对许多问题探索的连续性,即用另一种方式显示出它的“系统”性。这两方面,或许也适合史学以外的一些学科用以看待本学科的理论遗产。
中国古代史学家鲜明的理论意识,具有久远的传统。东汉班固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后论)这里既说到“事”,也谈到“理”。《后汉书》作者范晔一方面班固《汉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一方面夸耀自己所作的序论“笔势,实天下之奇作”(《狱中与诸甥侄书》,见《后汉书》卷末所附)。刘知幾更是“自幼观书,喜谈名理”(《史通·自叙》)。元初,胡三省一种说法,即“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胡三省尖锐地指出:“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亡弊。”(《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书首)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命题,了“势”与“理”的辩证关系。王夫之还指出,读《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又是从哪些方面,他写道:“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叙论四》)王夫之的势理观以及他从对历史的认识中所阐发的“论”,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理论的和深入的思考。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理论意识有久远的历史传统,而特点是阐发理论问题一般多与叙述史事相结合,这就是“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学人表述理论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学人思维方式的特点。
当代中国学人不仅有责任把这一理论特色展现出来,而且要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民族性的优势发挥出来。唯其如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才能建构起来。帮你看清已婚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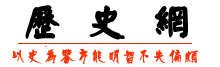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