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我的另一半为致敬并超越经典,讲谈社给新版《中国的历史》定下两大原则,一是研究角度出奇出新,二是叙事通俗易懂。
一套由日本学者集体所著的《中国的历史》丛书,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环球》记者近期走访了出版方讲谈社以及两位日本作者,一探丛书出版背后的故事。
讲谈社是日本最大的综合出版社之一,出版物涵盖文学、社会、哲学教、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门类,涉华题材是其历来较为关注的出版题材之一,至今出版过不少以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旅行记等为题材的图书。这套《中国的历史》于2004年至2005年间推出,属于讲谈社献礼建社百年大型策划作品之一。
“上世纪70年代,讲谈社就出版过一套10册的旧版《中国的历史》丛书。到初,旧版发行已快过去30年,而这30年间,日本历史学界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多新进展。有日本历史学者表示想出书介绍这些,讲谈社恰好正在迎接建社100周年,于是就召集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知名专家,策划、出版了这套丛书。”讲谈社第一事业局学艺部学术图书编辑组负责人梶慎一郎对《环球》记者如是说。
作为商业出版机构,讲谈社敏锐地捕捉到,日本社会重视中国,出版涉华题材图书是有市场的。据梶慎一郎回忆,“初以来,日中经济交流变得非常活跃,在旅游、商务等领域双边人员交流频繁,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很高。当时我们研判,在这个节点推出新版《中国的历史》,一定可以大卖。”
在日本出版界,中国历史在历史类图书中本就占据重要地位。据梶慎一郎介绍,日本历史类图书从大类上分为“日本历史”“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三大类。如此划分,和日本历史学研究领域有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学三大研究课题是日本史、西洋史和东洋史,东洋史其实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这种传统使得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拥有很厚实的基础,并成为出版界的一大品类。
旧版《中国的历史》,由当年日本最知名的专家执笔,堪称经典。为致敬并超越经典,讲谈社给新版《中国的历史》定下两大原则,一是研究角度出奇出新,二是叙事通俗易懂。
讲谈社就此邀请学习院大学教授鹤间和幸等4位专家学者组成丛书编委会。鹤间和幸在接受《环球》记者采访时表示,编委会最后确定的执笔人,都是在各自领域以新视角开展研究的学者,大家都不拘泥于传统的立场,尽量介绍新发现、新材料、新观点。
“有意思的是,负责新版的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是读着讲谈社旧版成长起来的。比如,旧版的秦汉史就是由我老师所著。这套丛书寄托了我们这代学者一种要写出不同于老师们的作品的情怀吧!这也是大家最用心的地方。”鹤间和幸说。
讲谈社以出版漫画起家,其社训是“有意思又有用”。通俗易懂,是这套图书的另一特点。“从一开始,我们就向执笔专家提出,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大众历史,大原则就是普者、大学生也要读得下去,不要写成艰涩的学术著作。”梶慎一郎说,“所选的作者,是有这种笔力的”。
《环球》记者查阅发现,新版《中国的历史》的10余名作者都是日本中国历史学界的一线顶尖专家,堪称各自领域的学术“担当”,学术功底厚实,治学态度严谨。这了丛书的学术可靠性,使其获得学界广泛认可。
比如,《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的作者——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平势隆郎,是日本东洋史学泰斗白鸟库吉的继承人之一,也是现今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集大成者。再比如,《始的遗产:秦汉帝国》的作者鹤间和幸,是日本的秦始皇研究第一人,其研究在中日两国学界都得到认可。
《环球》记者采访平势隆郎和鹤间和幸时发现,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在治学风格、历史观念、大众历史写作等方面拥有如下三个特点,这或许是这套丛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后脱颖而出的原因。
首先是突出的材料搜集、整理能力。在做学问方面,日本人也充分发扬了“匠人”,能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整理、分析庞杂的材料,并据此得出新结论。这一过程体现在书中,往往是抽丝剥茧,如侦探破解疑团一般,引人入胜。
平势隆郎的一大学术,是发现《史记》在编年方面存在疑团,并运用独创的方法,通过重新编排历史事件年份化解了疑团。他向《环球》记者表示,《史记》的这个问题是他年轻时发现的,为解决这个问题,他耗费10余年时间对历史事件年份进行了重新整理、编排。“这项工作非常耗费时间。那十几年,我每天下班后都在办公室整理资料,有时回过神来发现已是第二天早上。”
平势隆郎向《环球》记者展示了他当年整理的编年表,编年表由一张张泛黄的纸张粘贴拼接而成,长达10余米。
平势隆郎说,这个工作虽然看着很枯燥,但通过十多年的整理,他解决了《史记》在编年方面的疑团,一些新出土的中国文物材料证明了他的正确性。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一书中,我对自己的这个工作进行了介绍。在日本,有人评价我的作品‘虽难但有意思,像悬疑小说一样’。”他略感自豪地说。
鹤间和幸也表示,日本学者善于细致整理庞大繁杂的材料。“我年轻时做过汉朝士族研究,制作了地方士族分布图,标注何地有什么士族,相关材料整整有两大箱。”他说,“我的这一研究后来发表在了日本史学上,引起了中国学者注意。”
其次,除扎实的文献研究外,不少日本学者还注重行走历史现场,借文物说史,并能将新学科等不断运用到历史研究中。
1985年,鹤间和幸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在一年的期间,他前往西安待了3个月,考察走访多个汉皇陵,并结识了多位中国考古学者。
“我虽然不属于考古学者,但在寻访历史足迹的过程中,只研读司马迁的《史记》是不够的,要去寻访历史现场。亲身去走走看看,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行走历史现场的所感所得,在我书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他向《环球》记者表示,“我本人还沿着秦始皇东游六国的足迹,遍访全中国。这一经历也体现在了书中,我想所有这些对中国读者而言都是十分新鲜的。”
鹤间和幸虽然在日本做学问,但赴中国长期考察不下10次。他曾骑着自行车绕着西安城转,还争取到日本的预算,和中国学者一起调研黄土高原的自然,用自己的腿脚一步步去探索历史。
除寻访历史现场外,鹤间和幸还注重借文物说历史。鹤间在日本参与组织举办过三次大型兵马俑展览、中国文明展等,在书中,他利用简牍、帛书、墓志等材料,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秦汉世界,而不是仅仅记录文献中的历史。
鹤间说:“我还曾与NEC公司合作,分析了每个兵马俑的面部表情,证明世界上确实不存在完全一样的兵马俑,并和卫星图片专家一起研究黄土高原自然。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就能开拓出一片新世界,这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在探寻文献背后的历史。”
第三,研究中国历史,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相比中国学者,他们能够以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带给中国读者新鲜感;相比欧美学者,他们处于汉字文化圈,自古对中国的研究就有深厚的积淀。
鹤间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属于外国人,能够看到很多中国学者看不到的角度和观点。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能够从东北亚全局审视历史。
比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的作者杉山正明就是从外部世界来历史,从北亚、欧亚角度解读那段历史。再如,平势隆郎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一书中,提出了很多有待商榷但堪称中国国内史观的论点。
此外,鹤间说,相比,日本对中国而言属于同一汉字文化圈,不论在江户时代,还是明治维新时期,中国古文经典教育在日本都占有重要地位,日本人都是从小就要学习汉字。直至我们这一代学者,考大学也要具备一定的中国古文知识才行。
在日本,中国古典文献是上层社会教养的基本。平势隆郎的家族在历史上是日本大户人家,其家族历来重视《论语》等中国经典古籍的教育。他向《环球》记者表示,在他很小的时候,精通古汉语的父亲他学习五经,至今自己仍能流利《论语》。
向中国市场推销这套丛书的负责人,是讲谈社海外事业战略部部长刘岳。刘岳向《环球》记者回忆中文版本的出版经过时说,“我个人本身非常喜欢这套历史丛书,很希望向中国读者推荐,也很看好其销。”
讲谈社2005年成立分公司,刘岳当时担任分公司负责人。之后,讲谈社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于2014年出版了该套丛书。
对于中译本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刘岳称结果证明他预测对了,“这套丛书的视角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比如,现在中译本中销量最好的是宋朝历史那一册,这本书以平等的视角讲述东亚历史,这对中国读者而言无疑是出奇出新的。
“另外,这套书的中文版制作十分精美,连日本的作者看到中文版本后都连声称赞。实际负责的理想国团队不论是翻译,还是制作,都非常用心。”
谈及讲谈社与中国市场,梶慎一郎和刘岳都表示,讲谈社和中国市场的商业关系越来越强,今后将会有更多像《中国的历史》这类图书走进中国市场。
讲谈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和中国国内的出版社开展合作,如今在中国的业务越做越大。刘岳说,讲谈社这两年每年向中国出口的图书有130部左右,以翻译出版为主,今后将推出中日联合制作出版模式的图书,实现中日联手策划,中日同时出版。
·遵守中华人民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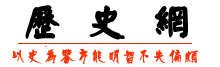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