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传奇的人物,他是文学史上的巨匠,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他是书法史上的名家,黄庭坚赞其“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他是佛教上的,摄取儒、释、道之妙理,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虽因党祸,而辗转迁谪,寥落人生,终不得志,却又长于诗文书画,而留下了千古印记。从两宋时代的“士大夫无不规摹”到元明历代对其或抑或扬,苏轼不仅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标杆”,更是事涉背景、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
宋朝尚文,文章书画,不仅彰显着文人士大夫的修身之道,也成为标榜清明风气的外在表征,所谓“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苏轼天资颖慧,幼年作《却鼠刀铭》,苏洵称之,“命佳纸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苏轼亦从其父,法晋唐,但并不拘于一家一道,黄庭坚评其“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可谓是书法之集大成者。
在宋人眼中,苏轼之书法“尚意”,而“妙在之外”,如其诗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虽用墨太丰,而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又“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在黄庭坚看来,苏子瞻书法得晋人韵致,非技法之高超,全在于“无俗气”而“韵有余”。这种“韵”得益于深厚的苏门家学,文章学问的涵养,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其后继者更将这种“尚意”多加阐释,如李之仪提出的“为上”,秦观讲求的“不以病其”,陈师道所言的“妙在心手,不在物也”,但在恪守者眼中,苏轼书意,强作横书,不斜则浊,即便是运笔方式,也是“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
苏轼之书为所重,除“笔圆而韵胜”外,更在于“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宋代士大夫讲求“胸中”和“腹中诗书”,既要胸中磊落,不随俗低昂,又要有忠义之气,临大节而不可夺。宋室南渡后,“元祐学术”逐步解禁,苏轼的气节开始为人所颂,宋孝更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追赠太师,并赞其“嶤然之节”。在《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又谈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苏氏文章成为一时之风尚,其书更成为争相摹习的楷模,遗墨字迹,万金购藏,更通过刻石、刻帖等方式,广为流布。南宋时代,独守半壁江山,士人关心国是,追怀节义品格,“立身大节,下睨,刚毅迈往之气,固宜磅礴八极”皆蕴藉在翰墨之间。
蒙元时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一派文人,推崇王羲之、王献之,又强调“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如董其昌所评“赵子昂则矫宋之弊 , 虽己意亦不用矣。”对苏轼并不十分崇尚,赵孟頫在《论宋十一家书》谈到:“东坡书,如老熊,百兽畏伏。”苏轼只是众书家之一,而非风尚。
明初,仍强调取法晋唐,轻于宋。周宪王朱有炖说“予平生不乐宋人书”,其所辑《东书堂集古法帖》,苏、黄、米、蔡无一入选。《明史·选举制》 中提及监生需“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国子监·监规》更是要求“点、画、撇、捺,必须端楷有体,合于书法。”追求“点画信手”的苏体,与务求的《监规》格格不入。
实际上,苏轼在民间仍有广泛的影响,虽“有欹倾狂怪之势”,但“坡老墨迹,三尺童子亦知敬之。”其墨迹经北宋崇宁、大观的,及四五百年梦见偷东西被发现沧桑,到明朝已弥足珍贵。文徵明见坡公书,有十余种,多已残损,《乞居常州奏状》虽小楷淳古,而剥蚀处多;如《赤壁赋》则前缺数行;《宜春帖子》又中失一纸;其《寒食篇》《芙蓉城诗》与《九辩》,皆削去题名。许多人为了一睹真迹,不惜深入穷乡僻壤,荒僻古寺,甚至冒雨前行,即便得到片纸,亦视若珍宝。
相比于宋人对高洁品行的格外看重,明人也“因人及书”,或景仰其人格文章,或其文章,或嵬集墨宝、刻石刻帖,以祝允明、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书家,更是以苏书为典范,欲取其长。祝允明“偶效东坡书”。文徵明早年亦效东坡,自恨天资有限,不得东坡之韵,只学得“偃笔肥墨”。王世贞评文徵明书,认为其“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岁取《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但书法成就远不及宋人。既缘于习书者的职业画家身份,不得不迎合市场与应酬之需,更为关键的是技法难习。对于苏轼而言,书法既是爱好,“如好声色”,也是随心之作,并未严格恪守晋唐规矩。明人却将“尚意”,视为可摹习的范本,“意”不同,习字的效果自然不同。黄庭坚曾评苏轼假画:“高述潘岐皆能赝作东坡书,余初犹恐梦得简是真迹,及熟观之,终篇皆假托耳。少年辈不识乃如此!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
近日,《竹石图》惊现于拍场,或真或赝,其韵难辨。既是“尚意”之作,除了坡公自己,恐怕都难以说清,而其“挟海上风涛之气”又岂是区区后辈小子所能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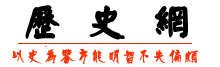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